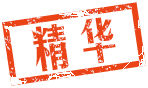|
二十七岁那年,我住一中的家属院。 原本是些三间一套的小院子,因为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小夫妻渐多,便拆了院墙重新隔断,三间变两间。单行的砖墙只是摆摆样子,隔不开洗菜做饭拌嘴的声音以及东邻西邻相互间的玩笑话,稀疏的木板门像栅栏,老式的木头窗户,院子里除了砖头铺的一条小道两沟葱之外,其他的地方青草不芟。也没啥家具,外屋是沙发,里屋一张床一个梳妆台,我的书,在窗台上堆得满满的。 平日里老师们去上课,院子里静悄悄,偶尔几个退休的老人在门外说几句话。后来,年龄同样相仿的小孩们渐渐脚步蹒跚,渐渐咿呀学语,让这里多出了几分热闹。 休班时,上午我就搬把椅子,坐在屋前的阳光里看书,葱苞子开花了,小蜜蜂们嗡嗡嗡地飞起飞落,草穗们点点头,偶尔在阳光里摇曳得晶莹透亮。路过的风懒洋洋的,门墙上,半开不开的金银花就吐出淡淡的香。 中午给媳妇做好饭。下午去一中的篮球场和几个球友老师打打球。二十七八岁的我还年轻,弹跳和爆发力也都还好,我喜欢那种假动作将防守者晃起来的感觉,喜欢飞在空中,换手,在防守者的手臂间的空隙里将球打进的感觉,自由、轻盈,仿佛心都飞起来。 傍晚是院子里最热闹的时候,人们拎着大大小小的水壶,去大门口东边的锅炉房打开水,来的,去的,碰头的打着招呼。 一天的时光,倏忽而过。 日子简陋却悠然,心,宁静而踏实。
二十八岁那年,午后的阳光正好。 在所有对岁月静好的回忆中,阳光,总是必不可少的,并且温暖明亮。央视电影频道有个节目叫“流金岁月”,我喜欢这四个字。流金,该是记忆里阳光的颜色吧。前两天,QQ上看到水姑娘的签名:阳光正好,吾辈尚在。心,就突然被轻轻敲击了一下。我说,签名真好,只是,应该改成:阳光尚好,吾辈正在。 有谁,知道那些金属般闪亮的阳光在我心中有着怎样的温暖。 而记忆里,那个午后的阳光,依然闪耀着金属般的光泽,洒在我身上。穿过阳光,穿过门口的102国道,我去家属院斜对过的小发屋剪头。闲谈中,女老板问我上高几呢,我回答我都二十八了。女老板冲里屋喊:××,你出来。她对象走了出来,女老板说,你看看,人家也二十八了,看看你,老爷子似的。 三十岁以前的我,头发又黑又有弹性,蓬蓬地,从来只穿牛仔和运动服,再加上埋头自我,不知世事,大概幼稚的只像个高中生。 三十二三岁后,脸上开始长斑,这点随了我爸。再过二三年,左鬓依稀生出了几茎白头发,这两年,更是抑制不住地满头茂盛起来,这点,又随了我妈。再不敢留长头发了,一短再短,如今去剪头,都叫他们用电推子推。 当年,在北京上学,爱摇滚,穿破了洞的牛仔裤,我还扎过小辫子呢。 回头看时,厚厚的日子堆积得那么多,却又那么不禁过。青春也罢,幼稚也罢,风一样就在我们身后远去。 媳妇笑我:还没机会成熟 ,直接就老了。
住家属院时,孩子很小,肩膀也就和茶几一般高。我们几对小夫妻的孩子都差不多,在一起,有伴,也热闹。
我这个人脾气好,对孩子却没耐心。小孩子也的确淘气,一刻都闲不下来。我在沙发上看书,她在茶几边淘气,说她,不听,还不听,我急了,一拍茶几扶手,大声呵斥她。谁知她竟然两只小手都拍在茶几上,对我怒目而视,大声叫:啊。那时她还不会说话。 不会说话的她,左右就一个“啊字。春风正暖的时候,我把她放到自行车后的小座里,慢慢骑行在河堤的柳丝里,骑行在一中操场边的白玉兰花下,我说,小姑娘唱,她在后座就“啊”,只一个字,完了。一会,我再说:小姑娘唱。“啊”,又完了。再说,没有了动静,回头看时,头歪在一边,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会说话了,话却没完没了起来,不管和别人还是和自己,听清听不清的,自顾自地嘟囔。我说,你这几年,比我这几十年说的话都多。一次,她坐在我的后座上,忽然说,爸,你看人家拿的是啥?那时正在八里铺小学的门口,我一看,边上的小孩子正在吃冰棍。 人小鬼大。 再人小鬼大,也毕竟是小孩子。傍晚吃完饭,我们三口子去散步,媳妇去了厕所,我们俩在大门口等。过往的老师问:你妈干啥去了?尿尿去了,小姑娘响亮而干脆地回答。人们哄堂大笑。走到一中院里,老师们逗她:你是哪来的,不许到我们一中来。小姑娘摇摇晃晃地抬起鞋子大声说:我踢死你。 隔壁的小公子小于,应该是小小于,从容而淡定,问他:长大了干什么?蹬三轮,他从容坚定地回答,神色悠闲。在我家玩够了,对他爷爷说:回家。他爷爷抱起他说:走,回家。他却说:爷,回家干啥。老爷子气乐了,不是你说的回家嘛。 前排的小姑娘爱美。人们见到总是逗她:瞧,哪来的小美女。她会骄傲地昂起头回答“哼,没见过美女吗?” 女儿小时候,我常下重手打她。那年冬天,她老玩自来水,凉水把袖子都湿透了。拉她回来,还去,再拉,还去,就是不听话。气得我拿筷子狠狠敲她的手背,都打出了血印子。可不知从啥时候起,我再不碰女儿一个指头了。我没有察觉这种变化,只知道,她的个子越来越高,如今,她已经高过她妈妈许多。我甚至和她说话,都轻声细语起来。 家属院,早就散了。00年的时候,卖给了进校,我们也纷纷搬了出去。一些人,更是越走越远,有的到了北京,有的到了天津,我们则先搬到了繁荣又搬到唐山。 转眼,已然过去了十二年。 那次回家,路过门口,已然面目全非,但我知道,那里,就是曾经的一中家属院。我放慢速度,凝望,高楼的下面,依稀还留着两排平房,只是,看不清,我住过的那栋,还在不在。木门前,我从老家移植来的那株金银花,是不是还爬满墙头,吐着淡淡的香。 2012、12、26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