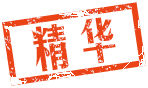|
老实说玉田对于一个很少出门的孩子来说,具有极大的诱惑力。那里有比韩家林多的多的人。饭馆里有比家里过年更香更好吃的饭菜。南高小里有比陈老师更厉害的老师,虽然他们手里并不都提拉着一根让人生畏的教鞭。 一次我背着家里纺好的麻经去玉田卖。爸爸怕我解不开,绳子结了一个活扣,一个人偷偷拉一下活扣上的绳子头。于是背着的麻经团,叽哩咕噜地四散滚落,我在人们的脚下拾,那个人和许多的人在笑…… 我又想起那三个小子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下捯我从15里外挑来的茅茅涨。 这种进城被欺侮之感,长久萦怀不去。 春天正是做工夫的好季节。我不得不再次去这个让我生厌,也让我有些恐惧的玉田。做工夫最重要的是能吃饱,我带出一张嘴去,家里的弟弟妹妹也能多吃一口。 玉田的工夫市我卖柴禾时过了一次。但我还没有真正上工夫市做过工夫。 小学课本里有哥伦布探险一课。哥伦布敢探险美洲大陆,难道我就不敢上玉田工夫市?去! 我设想了去工夫市的种种结局,恐怕不会有人敢抢我的锄和抿铲吧?那样的话我会把家伙当武器,谁先流血还不一定呢! 头天晚上,我把锄在碌碡上磨了磨,锄角秃成园形,开高粱苗锄角尖尖的才好使,凑合吧。 干不干三分样。戴一顶草帽,扛一把锄,裤带上别一把抿铲,这才像一个做工夫的。 夜里睡不稳,怕睡过站。 天蒙蒙亮,我爬起来。家里人还都睡着,妈说,多加小心,没人雇就早点回来。我说:嗯。 我摸出放在门后的家什,轻轻掩上门,再从外头掩上排子。 东边天际一条鱼肚白。四周远处还是黑黑的一片。道路像是一条灰白色的带子,牵着我向玉田走去。我回望有我尚温暖的家的韩家林,像是白色天边的剪影。偶尔传来一两声鸡鸣。 黑地里走路,无暇四顾。觉得时间不大就到了五里桥。桥边的王八驼石碑孤伶伶矗立着。王八嘴里有赶车人新抹的车轴油。据说是这样可以保佑不翻车出事。我心想,我要是那王八,有那大的道行,下桥就让他翻车。抹一嘴黑油恶心不恶心呀。 到工夫市已是天光大亮。 街面上人头攒动。看来还不晚,到的正是时候。 来做工夫的人,成年人居多,有孩子但看着都比我大。 我个儿小,不容易被叫工夫的人看见。我把锄杠直上直下地举着,看见锄杠就能看见我了。在人群里挤来挤去,挤了几个来回, 也没人理我。 人越来越稀了。还是没人理我。我想:够呛,怕是真的要剩下了。心里往好处想:原来一些凶险的预想都没有发生。 我有些懊丧,十五里地走来回,挤了半天工夫市,饿肚子不说,这半天算白搭了。 工夫市没什么人了,我也准备往回走。过来一个四五十岁的城里人,领着几个扛锄做工夫的。他拍拍我的脑瓜顶:薅谷子去不?他说了工钱,大约不到一个大工夫的一半。我心里高兴,钱多少小事,有地方吃饭了。我说:去。 他家住东关路北。一行人跟他到家去吃饭。小米稀饭,咸菜,摊糊饼。我边吃边忖思,玉黍苗、高粱苗都薅过,谷子苗没有薅过。啥样呢?又一想,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走?别人咋干咱咋干。照葫芦画瓢呗。 他家的地在东关外王家家庙的东边。大约是现在玉田三中的地方。 做工夫中的一个人问:薅啥样的,是“一条线”,还是“满天星”? 东家说;一条线。 众人一字排开,一人一条垅开始薅。 我把黑壮的苗留下,尽量让它们在一条直线上。 东家逐个检查过来,他一把拽起我来,大喝:你把谷子都薅啦!留下都是谷谷莠子!你走吧,白让你吃了一顿饭。 我站在他面前,一声没吭。 他把一棵被我薅掉的谷子苗举到我的眼前:这才是谷子,裤儿上有毛的才是! 我心里懊丧,让人家休了。白吃了人家的饭,还薅掉了人家的谷子。幸亏没多远,薅多了包赔不起呀。 谷子怕涝,产量低,韩家林种得少。可我还是认识谷子了。 原路返回。下五里桥走到行宫南和尚坟附近,道北,俩个中年妇女在薅谷子。看见不远处走过来的我,说:“小伙子,是让人休回来的吧?” 我说:“人多,没下去。”暗想,睁着眼说瞎话,有违五戒(杀盗淫妄酒)之一的妄字了。 “薅谷子中不?” “中。”我走过去。又说了工钱,好像是比工夫市上的要多点。 年长些的妇女说:“地头笼筐里有发面饼子,水罐有水,你先吃点。” 我吃着发面饼,看她们薅的谷子。谷子叶片伸出的裤的地方,有茸毛,而谷谷莠子裤的地方是光滑的。这和粳子与裨子区别的地方是一致的。而谷谷莠子要比谷子长得壮长得黑。这一点也和粳子裨子区别相同。为什么野生的草要比庄稼苗长得壮,长得好呢?我幼小的心灵里还参不透这个理儿。 吃完后,我按她们“一条线”方式薅起了谷子。 我有薅玉黍苗的底子,认识了谷子后薅起来就快了。 她们俩看了我薅的谷子说:“这小伙子干活还不赖。” 我留的苗正,距离相当,真是一条线。我说:“干这样的活计还能让人休回来?” 两个妇女笑了:“跟你说着玩呢。” 她们是北面查屯的家。因离家远,中午也没回家,我们三个就在地里吃发面饼子。吃完了接着干。 日头平西前,一块地薅完了。我虽然比她们要小许多,但活干得比她们并不少。 年长妇女说:“回家吃点饭去吧。” 我说:“不了,回去晚了家里惦着。我就直接回去了。” 她们也没有深留,把工钱给我就各自回家了。 查屯在正北,我向东南。两个中年妇女我不知道她们姓字名谁。多少年过去了,这两个身影已经模糊不清了。她们还能记得那个当年做工夫的孩子吗? 很多人和事都忘了。谷子和谷谷莠子的区别还记得很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