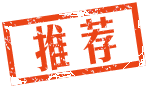|
几乎每天都去的广场上的树越来越凋零,前几天落了一地的银杏树叶金黄金黄的,我觉得前些天的冬天还不算太苍白;而现在,除了几棵孤单的法国梧桐还索索的把干涩的树叶裹在身上,就只有些柳树抖落些枯叶在石板路上,踩上去嚓嚓的声音,没有春、夏和秋天柔柔的味道。 照惯例冬泳五十米,又在广场五百多米的硬石板路上跑了十二圈,才停下脚,发现几个人在一个老槐树上弄着什么。我走了过去,看见那几个人把一个铁牌子围在树上,牌子上写着“古冶区古树监管对象”牌子上注明了树的品种,监管电话和单位等等,和工作的人打听后我知道,这个广场上有四棵这样的槐树。这些树据说都是解放前就有的,具体树龄工作人员也搞不清。 我今天才认真注意这些树:树不算太高,差不多一抱半粗,树干上没多少枝,树皮龟裂,有的树干已经有了一些裂缝,他们都被一圈方石圈着,树干上缠着霓虹灯。和移植过来的树不同,他们显得特例,有一种没有修饰的自然和从容。临着他们旁边,被修剪过的柳树打半腰就被截掉了头,虽然柳枝一到春天葱葱茏茏,可是少了河岸边柳斜向水面的妖娆。远远地看上去就像一截木棍顶着一个大圆球。在我家附近有一个饭店,也有一颗粗粗的大柳树,从前到了春天,树枝肆无忌惮的四处长,柳条垂到房檐,树叶打在窗上。后来因为饭店生意不好,饭店老板请人算了一卦,说是这棵树的问题,只有把树头给锯了才能发达。柳树被砍了头,饭店的生意似乎应了算命的话渐渐红火了,我却觉得这棵树奇奇怪怪的。等过了三四年,树顶的柳枝又长满,前年夏天,我在饭店门前学车,拿一把凳子坐在树荫下,柳树条低低的抽我的脸,抬头看着突兀的树干和十几条滋生出来的枝,我不知道哪个是新树头。 今年,饭店老板去世了,只比我大几岁。后来听别人说,自家的柳树千万别去了头,不然会不好。我不是唯神主义,但我还是有意无意把这件事往柳树被锯了头上靠。 夏天和骑友去迁西尚庄,见过两棵古树,一棵槐、一棵松。槐树在松树西边,临街而立,树干中间空了,可是树冠硕大。远远看去,像一个老人弯着腰,把双臂展开,等着拥抱来朝拜的人。树上的说明说,这棵树已经千年,历经战火而不倒。如今成了四方膜拜的神木。抬头看,树叶中还有数不清的类似扁豆形状的包,这是我从没看见过的。不知道这树小的时候有没有被人修剪,如果修剪过的话,也许不会是这种虬然的姿态。等见到了松树,远远地看上去似乎是四五棵松树等到了近前我呆住了,它哪里是树,它是一张大伞,方圆三四十平米的大伞!树干在当中,另外几棵都是水泥柱子,是村民担心向外延展的树杈折断用来支撑的。我呆在树下,松树也望着我。我抬头看见松树杈的缝隙中有些青苔,青苔上有一枚黄色的小花,这是生命奇迹吧,让它长在古老的躯体上。 也见过老家兵营大墙边的老槐树,和古槐差不多,大多中空,有的就靠在墙上,有的歪向街道。早春的风,夏的雨,都没让他们折断,在树下走过的人不担心。槐树花开了,扑头扑脸香。夏天,有一些不知道名字名字的藤拴在树上,等到了冬天,他们还不掉下去,依旧蒙着槐树,像一张网,有的树上也许会有一两个雀窝,有的大有的小。这些槐树除了我们小时候淘气折过一些槐花以外,都是自由自在的生长的。他们或粗、或弯。或斜、或直都不关人的事。 和我妈家隔着一条街道,老早以前种着一棵柳树,已经很多年了。柳树旁边是一个小菜园,红红绿绿的菜满院子。柳树占的地方不小,夏天总有一些人在树下聊天。大前年我发现那棵柳树没有了,剩下一个树桩,挨着树桩停着一辆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