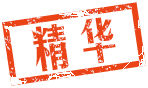|
|
玉田县文史工作的奠基人——孟昭林
李作仁
孟昭林,1926年10月25日生于玉田县彩亭桥镇梁庄子村,满族。国家二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河北分会会员,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副研究馆员。唐山市第八、九届人大代表,玉田县政协第二、三届常委。
孟老早年就读于河北省立滦县师范学校,毕业后最初任教师。1953年到河北省文化局工作,期间曾参加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全国考古工作训练班,听取了郭沫若、裴文中(班主任)、贾兰坡、梁思成、陈万里诸多名家授课,收获颇丰。后回原单位从事考古工作数年,相继发表文章20余篇。
1960年与一批省下放干部到玉田,任职搞农业二年。后调入玉田县评剧团,担任编剧15年,创作、改编剧作10余种,发表4种。
其后,又在鸦鸿桥中学、林南仓中学、玉田县文化馆等单位工作。
孟老多才多艺,体育、音乐、戏曲、写作、书法无所不好,无所不能。广泛的爱好,深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使他后来搞起文史工作来得心应手,左右逢源。
对玉田县文史工作的贡献
县政协文史工作的顶梁柱
文史资料工作,是曾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同志于1959年倡导的。它具有“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社会功能,是人民政协工作中的组成部分。
玉田县政协自1981年第一届委员会开始,就设立了文史工作组,着手文史资料的征集和整理工作。从第四届开始(1990年)建立文史委员会,使其工作更加规范,人员更加充实。经过几届政协委员、文史资料员以及社会各方面人士的大力支持,从第一届政协(1981年开始)至第五届政协(1998年结束),共征集、编辑、出版《玉田县文史资料》六辑,发表文章164篇,计57.7万字。这是玉田县政协的一项重要成果。它不仅为修史、编志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文史资料,而且作为文史读物,也帮助了全体政协委员及广大群众了解过去,认识现在,从而激发了他们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感情。它是当时玉田县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
孟昭林先生是第一至四届县政协委员(第二、三届常委),期间,一直被分在文史组(后为文史委员会)。从此,他与文史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先后参与了第一、二、五辑文史资料的撰写和校对工作,而第三、第四、第六辑文史资料的征集、编辑、校对、出版等一系列工作则由孟老全面负责。他在《玉田县文史资料》上共发表文章14篇,计有《我的皮影艺术生涯》、《建国前玉田职业戏曲班社述要》、《猴戏大师郝振基生平》、《沈官屯完小创办初期见闻》、《游击环境下的六中和五六联中》、《清代玉田驻防营及其满族人史料初辑》、《僧尼生活八十年》、《孤树枣史料》、《刘玉春年谱》、《写实派猴戏一代宗师郝振基》、《昆坛翘楚王益友》、《达王庄益合科班若干史料辨析》、《享誉北昆舞台的四代人——介绍梅花奖得主侯少奎一家》、《工艺美术师张国富及其作品》,共约4万字。被唐山市政协选用7篇。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末,即第一至第五届政协期间,是我县文史工作的辉煌时期。在此期间,孟昭林先生始终投身其中,不仅亲自采访、撰写了许多有份量的文章,而且负责文史资料的征集、编辑、校对、出版等工作,为此,他花费了大量心血,起到了顶梁柱的作用。可以说,他是玉田县文史工作的奠基人。
历经十年潜心研究北方昆曲史
昆曲,亦称昆剧,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元代产生于江苏昆山,因此得名。昆曲分南昆和北昆。流行于江苏省南部的称南昆,流行于北京市及河北省一带的称北昆。而玉田县则是北方昆曲的活动中心之一。
孟昭林原来对北方昆曲也知之甚少,只是从袁竹安等老先生那里听说过一些概况,也看过一些相关的文字资料,但因为这些史料都是辗转相传,不免异说纷呈。同一个问题,往往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哪一说法可靠,难以定夺。酷爱戏曲艺术的他产生了一种想法:玉田县究竟有哪些北昆班社?培养了哪些北昆演员?他们都有哪些演出活动?主要剧目是什么?这些问题一定要搞清楚!于是,从1984年开始,他对京东北昆的历史进行了长达10年的调查、研究和探索。
此前,孟老了解到,早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县城东南的达王庄,举办过一期昆弋益合科班,培养造就了一批身手不凡的“益”字辈演员,此后,以这批演员为骨干,兼邀北京及京南演员,曾多次组织昆弋班社,演于京东各地,有的还进入北京,名噪一时,使玉田成为我国北方昆弋的重要活动基地之一。于是,他骑着自行车前后10余次到达王庄,以及周围的裴官屯、丁官屯、李官屯、张官屯、东高桥等村,深入群众,遍访当年班主的后裔、族人,反复核对相关史实。七访丰润县压库山,到遵化县王家铺,专访基顺合班负责人崔连合之子崔印宽,了解同合班与基顺合班的情况。与此同时,还专程到北京,三访北昆著名花脸演员侯玉山(93岁),三访北昆老艺人王鹏云(75岁),五访北方昆曲史家朱复,他们中有的早年就在各县职业戏曲班社,为孟老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东西;另外,与北京北方昆曲专家张秀莲、天津戏曲研究所戏曲史权威王永运、北昆表演艺术家侯少奎多次书信往来,获得了大量珍贵资料。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孟昭林不辞艰辛,锲而不舍,经过断断续续10多年的调查、访问、研究、探索,终于将在玉田县境内的北方昆曲班社、主要演员及其演出活动情况基本搞清,撰写出《京东玉田——北方昆弋的重要基地》、《京东同合班与基顺合班新探》、《郝振基和他的猴戏》、《京东昆弋源流及其盛衰概述》、《北方昆弋名演员生卒年考辨》等30余篇有价值的文章,约5万余字。另有2万余字的《京东昆弋访问录》(未刊稿)。这累累硕果,填补了北昆研究领域的空白,引起了北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也使孟昭林成为京东北方昆曲研究的权威人士。
完成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丛书
1986年,孟昭林调到县文化馆,接受了编辑《唐山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丛书?玉田卷》的任务。他刚一接手时,简直令他头痛,只见那征集来的稿子,除少量几篇还象点样儿外,大多数语句不通,结构松散,甚至有的仅仅是一份素材而已。面对这样一大堆粗糙凌乱的“初稿”,推掉不可能,着急没有用,所以只得坐下来,耐心细致地一篇一篇地阅读,一句一句地修改,有好多篇甚至要全部推翻重写。后来经请示领导,给他派来一位帮手高玉顺同志,这才算减轻了他一些负担。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终于编辑完成了《玉田民间故事选》(56篇)、《玉田民间歌谣选》(43首)、《玉田民间谚语选》(139条)三本书,共10万余字。这套丛书的完成,使我县的民谣、民谚和民间故事得以保存下来。
耄耋之年担纲主编《玉田百年文化纪事》
1989年,孟昭林根据文教局领导的意见,着手编写《玉田县文化志》,经过4年的努力,完成初稿。但由于种种原因,该志未能印刷出版。时隔二十多后的2011年,他老骥伏枥,不甘寂寞,认为原来那份文化志初稿,如果湮没了不能面世,太可惜了!在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他决心自筹资金、自己主编一部像样的专著。于是,搁笔多年的他,披挂上阵,在原稿的基础上,重新编排组合、扩充内容,并且变一家之言为多家之言,在保留自己撰写的大部文稿外,邀请相关文化部门领导和知情者,操笔撰写相应文稿。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众多热心朋友的支持帮助下,一部包括文学、戏剧、电影、群众文化、民间文艺、人文景观和文艺理论七大编,共25万字的《玉田百年文化纪事》终于编纂完成。目前已进入排版阶段,预计将于今年上半年出版发行。该书全面具体地反映了1898年至1988年我县百年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而且图文并茂,填补了玉田县百年文化空白。87岁高龄的孟昭林先生又为我县文化建设做了一件大事、实事。
纵观孟昭林先生的晚年,即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30年来,一直从事着玉田文史的采访、调查、研究、撰写、编辑、出版工作,为此他一丝不苟,呕心沥血,取得了累累硕果,填补了多项空白,为我县文史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史工作者的榜样
孟昭林先生在文史工作方面取得了卓异的成就,在他身上具备了一个文史工作者许多应有的素质。
首先,具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文史工作的特点,就是要搜集、整理戊戌政变至“文革”这段时限内的口碑史料,并强调“三亲”,即亲历、亲见、亲闻。因此,如果不及时抢救,就会随着知情者的故世,失而不能复得,就会铸成遗憾。
我县皮影演唱艺术家张茂兰,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名满京东和东北三省,被誉为“皮影大王”。他1935年东渡日本灌制唱片,1944年投奔解放区,参加新长城影社,1949年赴北京参加第二届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1960年被聘为唐山戏校唐剧班的第一任教师……在皮影艺术方面的成就非同一般,称得上是皮影界的名人。1985年,孟昭林听说这位老人已经89岁高龄,就向其子、在县图书馆工作的张瑞琪建议:将张老先生的皮影艺术生涯整理成文,留下老人那段辉煌。得到同意后,花甲之年的孟老就同张瑞琪一起骑车前往蛮子营乡的小定府村(现为杨家套乡),往返80里,走访了张老先生。当时,老人虽已双目失明,但记忆力惊人,许多细节都能一一道来,这使孟老备受鼓舞,回来后就根据笔录一口气写成了1.3万字的初稿,由张瑞琪补充了一些细节,后又经孟、张二人彼此切磋,多次修改,终于成篇,题目是《我的皮影艺术生涯》(张茂兰口述、孟昭林、张瑞琪整理)。但就在这篇文章刚刚脱稿,尚未发表之时,张茂兰老人谢世了!悲痛之余,应该庆幸的是,老人光辉的皮影艺术生涯总算被“抢救”了下来,留给了后世。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史料,先在《玉田县文史资料》第一辑上发表,后又被《唐山文史资料》第七辑、《唐山戏曲资料汇编》第三辑等多种书刊转载。
自此以后,孟老凡是获悉史料线索,就尽快出访,并尽快整理成文,以便发现问题,再去补访。1988年,获悉孤树村尚有一位枣商袁德永,学田庄还有一位老尼姑安庆,都已八、九十岁,于是他及时走访,并立即整理成文。结果,把这些宝贵史料都“抢救”了下来。
对此,孟老常说:过去我们没开展这方面工作,也就罢了;现在,有政协机关每年拿出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就不能让一些珍贵史料,眼睁睁地从我们身边失掉,这就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其次,不迷信权威著述,敢于叫真儿。
关于达王庄益合科班的主办者(即班主),见于著述与文章者,多为“王绳祖”。这里有三个例子:一是1983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中“戏曲教育”条内写道:“由王绳祖在河北玉田主持的益合昆弋科班……”;二是韩世昌口述、张琦翔整理的《我的昆曲艺术生活》一文(载《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十四辑)在谈及著名昆弋武生王益友时写道:“幼时入王绳祖、徐廷璧组织的益合科班学武生”;三是傅雪漪撰《北方高腔浅探》一文(载《河北戏曲资料汇编》第六辑)也说:“玉田县则有王绳祖所办益和科班。”面对这些权威著述,孟老并未轻率相信,他数次骑车前往达王庄,深入王氏后裔,采访、核对。据王宗丰老人(属王氏二十世)说,其曾祖父同胞兄弟三人:长名绳,次名绶,再次名綖。这完全符合我国传统起名习惯,且都为“纟”旁,颇为考究。至此,孟老并未罢手,根据线索,又亲自骑车到城东北20里外的大狼虎庄找到王宗池老人(属王氏二十世),查阅了他保存多年的祖上传下来的《玉田王氏族谱》(原谱),看到族谱三门十六世王敬德条内写道:“敬德……配李氏……生三子,绳、绶、綖”。印证了王宗丰老人的说法,这才放心。那么为什么会有“绳祖”之误呢?只见该谱三门十七世王绳条内写道:“绳,行二,字祖武,又字正斋,生于道光十年庚寅九月二十七日丑时,卒于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又八月二十三日亥时,享年七十一(寿)。”由此可知是因为辗转相传,误将王绳之名与字混到一起了。
著名北昆演员郝振基,17岁从京南来到玉田县。入达王庄王绳主办的昆弋益合班,拜师徐廷璧学艺。那么,他的原籍究竟在京南何处呢?见于文章著述者,竟有四五种说法:一是大城县(见1981年出版的《中国戏曲曲艺辞典》“郝振基”条);二是代城(见陆萼庭著,赵景深校《昆剧演出史稿》);三是霸县(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郝振基”条);四是文安或霸县(见齐如山《谈吾高阳县昆弋班》一文载《河北戏曲资料汇编》第六辑)。此外,还有“高阳郝振基”之说,等等。
关于郝振基原籍的纷纭之说,虽说都有一定的权威性,但在孟老看来,哪个也无法轻易相信,只能靠自己脚踏实地地去查访。他先从郝振基之女郝富兰老太太(当时71岁)那里起步,据郝老太说,其父是京南抬头村人,但不知是哪县。后来孟老又从北京北方昆剧院高龄老艺人侯玉山(当时97岁)那里得知,郝振基是河北省大城县抬头村人。不久,又得到解放前的一篇名为《郝振基》的短文,也是如此说法。看来是确切无疑了,可以结束了。但他又想:这个抬头村究竟在何方?早年抬头村属大城县,现在未必仍属大城县。他仍不罢手。后访到一位郝的生前好友、达王庄早年驶船老人冯贵荣(光绪十四年生,当时96岁)。冯说,郝的老家抬头村,在胜芳镇东南8里大清河南岸。并说,当年他在那一带驶船时,曾得到郝的侄儿照料等等。接着,孟老又根据1981年河北省测绘局绘制的《河北省地图集》按图索“骥”,果然在地图上找到了抬头村。但它已改为镇,并已划入了天津市静海县的版图了。就这样最后确定:郝振基的原籍为大城县抬头村,该村现已改镇,属天津市静海县。
孟老就这样,不迷信权威,不迷信书本,而是靠自己脚踏实地,一处一处一人一人地去走访,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解决,理直气壮地纠正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等权威著作的一些错误,还其事实真相。其他如是“益和”还是“益合”?益合班何时开办?等等,都是下这样“狠”功夫搞清楚的,最后撰写成《达王庄益合科班若干史料辨析》一文。该文发表后,立刻引起了京津有关部门的强烈反响。北京昆曲史学研究社来函询问,天津市艺术研究所为此派两人专程来玉田拜访孟老。后来他们凭借孟老的研究成果为郝振基立了传。
第三,不畏劳苦,锲而不舍。
孟昭林青年时代从事过五、六年的考古工作,这工作和搞文史有某些相似之处。他说:那就是坐要坐得住,动要动得起来。即在需要查阅资料研究问题或撰写文稿时,就要坐得住,所谓有“坐冷板凳”功夫;在需要调查走访时,就要动得起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得设法克服。
孟老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这里举两个事例:
其一,孟老在研究京东两大昆弋班社(同合班与基顺合班)时,屡见诸家著述,在1917年进京演出这一问题上,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基顺合班,有的说是同合班;有的说这个同合班是由京南来的,有的说是从京东去的。简直令人眼花缭乱,孟老搞了三年也未搞清。直到1987年春节临近时才发现了一条线索——在丰润县压库山。于是决定前往调查。压库山是位于丰润县城西北的一个小山村,距玉田县城约80里路。当时正是严冬季节,第一次去调查、采访,家住东关63岁的孟老怕半路拦车没坐儿,只得跑到西关汽车站乘车,到丰润县城西面的高丽铺下车,还要往北步行5华里才到压库山。因为不是本县的村子,不好意思吃派饭,一直采访到下午两三点,才饥肠辘辘地步行返回高丽铺吃点东西,然后乘车返回玉田。为什么去压库山?因为压库山在清末民初是昆弋高腔戏班的“热窝子”,那里不仅有几位知情的高龄老人,还有两位当年同合班的老艺人——王成永和金长计,因而有指望把问题弄清楚。所以孟老不辞辛苦,抓住不放,连续出访,直到第七次才把问题搞清楚,写成《同合班与基顺合班新探》一文发表。这就是七访压库山的故事。
其二,1988年秋,为了撰写一篇反映尼姑生活的文章,孟老与政协机关的一位同志到韩家林乡的学田庄(现属亮甲店镇),两次采访一位八十岁高龄的老尼姑安庆。当想整理成文时,发现仍有几个问题把握不大,于是他又单独去了一趟。最棘手的是庙(即当年的尼姑庵)的名称,孟老遍访全村老人,谁也说不准,有的说叫“关帝庙”,有的说叫“娘娘庙”,安庆老人则说叫“菩萨庙”。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寻找早年的庙碑。还算不错,最后在庄东的小桥上找到了,该碑已经作为桥板铺在那里,不巧的是,碑文朝下,需要钻进桥洞才能看见。而这是一座小桥,桥洞很狭窄,只能匍匐而进,可桥洞里满是村民扔的烂菜帮子,还有一堆堆鸡毛。当时孟老穿一件蓝色呢子大衣,要爬脏乱不堪的桥洞,还真有点儿犯怵。但是,为了弄清庙名,他不顾这些,只好屈尊而进了。糟糕的是,当他好不容易爬进去后,才发现翻不过身来,仍然看不到碑文;只好又爬出来,再仰着身子进去。他终于看到了碑文:“重修学田庄娘娘庙碑”、“大清道光五年”字样。这时的孟昭林笑了。因为他在烂菜帮子和鸡毛上总算没有白爬,终于找到了他最需要的东西——准确的庙名:娘娘庙。这是他最开心的时刻!事后,他撰写成《僧尼生活八十年》(安庆口述,王学占记录,孟昭林整理)一文,刊登在《玉田县文史资料》第六辑上。
第四,开辟新领域,从不炒冷饭。
孟昭林先生所撰写的文史资料,都是通过自己亲自采访相关当事者之后根据笔录并参阅有关文字资料整理而成的,他从不重写别人写过的人或事。在他看来,只有写别人没有写过的东西,开辟新的领域,文章才更有价值。他对文史界出现的剽窃现象,深恶痛绝。他认为:将别人辛辛苦苦调查采访后写成的文章,拿过来改头换面装入自己的“文章”,是窃取别人劳动成果的行为,是不光彩的!当他花费很多心血写成并发表了《猴戏大师郝振基生平》后,1989年,在一本名人传里,忽然发现了一篇名为《郝振基》的文章。一看,其内容与自己写的完全相同,甚至连许多语句也未改变多少,而作者却是“王XX”。孟老对此非常气愤,鄙薄得很!他曾多次与笔者谈及此事,认为这纯属招摇撞骗,欺世盗名,是不道德的行为。
孟昭林先生与我是多年的老朋友,是我在玉田文史界最佩服的人。这不仅是因为他主持玉田文史工作多年,撰写了数十篇有价值的文史资料,对玉田文史做出了重要贡献,更是因为他治学严谨,务实求真,不迷信权威,锲而不舍,不走捷径,具备了一名文史工作者应有的美德。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我不敢说孟老已经达到了某一领域的顶点,但我坚定地认为:他,就是那种在崎岖小路上,不畏劳苦、勇敢攀登的人。
孟昭林先生是我县文史工作者的榜样。他的敬业精神,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
2012年2月21日
(本文首发于《种玉田》文史网刊创刊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