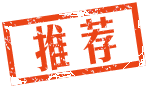|
|

楼主 |
发表于 2012-4-19 21:09
|
显示全部楼层
| 来自北京
三、风乍起:清前期诗歌
从历史分期来讲,清代通常被分割成两部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前为古代史,后为近代史。从文学史的眼光看,清代虽属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黄昏,但现代文学只是一抹晨曦。晚霞依然灿烂,天空更加绚丽。而丰润古代诗歌,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清代诗歌。因此,对于1840年至1911年的近代史,我仍放到丰润古代史里,《丰润古代诗抄》,自然将“近代”诗篇毫不犹豫地纳入其中。对清代丰润诗歌创作的分期,与一般文学史也小有不同:我以为顺治、康熙两朝的近80年,属清朝奠基时期。就全国而言,清代前期的诗歌,以反映民族矛盾为其主流的。但对于丰润而言,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虽然史料记载,清人入关后在丰润圈占土地也很严重,民族矛盾激烈,但诗歌创作中没有强烈的民族情绪。我以为,首先,是“避席畏闻文字狱”。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指出:“清人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有盗心。”其次,与这些诗人十之八九从大大小小的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又进身为大大小小的官僚地主有关。他们的屁股和朝廷坐在一条板凳上,似也无可厚非。这,与江南文人的激烈反抗并在诗文中有所表现形成鲜明的对照。
“都下三曹”
“都下三曹”,按《畿辅通志》,指清初丰润人曹鼎望和他的两个儿子曹钊、曹鈖。据说,当时文坛士林,因其文采飘逸,成就优异,故以“都下三曹”称之。 清初著名文学家尤侗在为曹鼎望三子曹鋡诗集《松茨诗稿》撰写的序的中写道:“丰润京畿壮县,与右北平接壤,予昔司李其地,出门即至,见其山水深秀,陈宫一峰介盘龙、大房之间,意此中必有贤者,后果得冠五太守而奉教焉。”崇敬之情充溢其中。
我以为,“都下三曹”,是开启丰润一代诗风之人。
曹鼎望(公元1618—1693),字冠五,号澹斋。顺治十六年进士,曾任安徽徽州府、江西广信府知府、陕西凤翔府三地知府。著有《曹子全书》、《艺文志》文集诗稿四十余卷。曹钊,字靖远,号眉庵,贡生。鼎望长子,著有《鹤龛集》、《剪波词》。曹鈖,字宾及,号瘿庵,鼎望次子,以贡生选任内阁中书舍人。诗文有《瘿庵集》和《黄山游纪》传世。
“都下三曹”这个名号,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邺下三曹”。于是觉得古人也是以此来比附的。用此三曹,照应彼三曹的曹操、曹丕、曹植,想来古人吹捧人的方法也很可爱。此番遐想真的在清代大文学家尤侗那里得到验证:他赞美曹氏弟兄时,曾说“信乎兄弟擅场,皆邺下之后劲也。”可见,“邺下后劲”之足,全然不管能否与其祖宗相较。再有,按敦诚赠曹雪芹诗句:“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而曹雪芹与丰润曹又是本家,甚至他的祖父曾称丰润曹是“骨肉”,这种照应就有了源流关系了。当然,如此捧场,估计“都下三曹”不会不高兴。
不过,“都下三曹”,我觉得实在也应当是“四曹”,丢下了曹鼎望的三子曹鋡,未免不妥。曹鋡,字冲谷、号松茨,由贡生候选国子监主薄、官理藩院知事。著有《松茨诗稿》和《雪窗诗集》。
民国时人徐世昌编的《晚情簃诗汇》中,称曹鼎望“诗近晚唐”。那么晚唐诗风是何等模样?有专家认为晚唐诗风是“感伤沉郁的主调、绮艳幽密的情怀、清丽工整的语式、思远韵永的风神”。听起来有点抽象且拗口,我们不妨去读一读小李杜的诗,就明白了。我倒是觉得曹鼎望的诗非近晚唐,而是更近魏晋。他有一首《汉口别舍弟》:“汝从燕马去,余向楚州来。归梦随江水,离愁入酒杯。暂分鸿雁亭,先到凤凰台。有约迟冬杪,斋头看腊梅。”既有生命苦短,酒助离愁,又有有约冬杪,斋头看梅的积极态度。与乃祖魏武属于同一个格调。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慨叹中,也不乏“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气概。顾随先生说“曹操是英雄中的诗人,杜甫是诗人中的英雄”,此处可见一斑。建安风骨,说到底,就是这种人生哀伤与建功立业“慷慨多气”结合交融在一起的。同时,这首诗风格疏朗自然,不事雕琢。这与晚唐也有明显区别。曹鼎望有一首古风,题他的“松茨园”,其序云:“东郊别业有松四棵,霜皮黛色,交盘若屋,颜曰松茨,时或栖止其中,不知身在人间世矣。”其诗云:“四松如高士,卜筑依左右。翠盖笼阶砌,凉颸生户牖。我来坐其中,涤尽心舌垢。……倦羽不思飞,爱止是林薮。策杖时相过,俨然成五友。秋蝉咽高林,白云幻苍狗。悠然远市嚣,渐觉空诸有。” 颇能代表他诗作的总体风格,读来也有陶令的超然世外,冲淡平和之感。曹鼎望诗忽而苍凉,忽而恬淡,有力量,不媚俗。五言尤其干净老辣。幸甚至哉,此松茨园又经重修,已然成为丰润一处诱人的人文景观了。
曹鼎望还有一个花絮式的小诗,即“千里捎书只为墙,让他一尺又何妨”的“让墙诗”。当然全国有十多个版本,明朝就有两个版本。但曹鼎望这首诗,在丰润民间广为流传,并堂而皇之地载入《浭阳曹氏族谱》,更为有趣的是,那个“让”出来的“仁义胡同”,那条一米来宽,百米多长的小巷至今犹存。所以,史有其事是不容置疑的。但可能与古人暗合,抑或借用了前贤文章?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说,曹鼎望的诗恬淡自然,不事雕琢的话,那么,曹钊曹鈖曹鋡的诗,就比较注重了文采。正如“邺下三曹”,曹丕和曹植,就有了“文的自觉”一样。而这种“文的自觉”,正是艺术追求的华美。这不应当算作问题。“诗缘情而绮靡”,“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也是“道”,而不能看作“术”。问题在于分寸,在于度。曹钊在“诗抄”中收录的诗作,差不多是乃父和两个弟弟的总和,达52首之多。县志上说他“性恬静,一生沉逸于山水林泉,诗酒自娱,工于诗词,”还说他“不慕仕禄”。在后一点上,我觉得还有相反的判断。他曾在《览镜》中写道:“尺蠖不成龙,尺水不成浪。览镜莫沉吟,本乏封侯相。”这种自怨自嘲,怕不是“不慕仕禄”,而是慕仕禄而不得。当然是什么原因使他没有进入仕禄之途,则是另一个问题了。他毕竟安于了自己所处的境况。他的诗每有佳句,令人神往。如,“鸟巢芦荻雨,人坐藕花风。踪迹烽烟外,生涯云水中。”(《唐溪杂咏》)像“大野平分瞑,危峰欲割云”(同上),也显出了生动中的精致。他的“编茅人境外,松际见孤亭。泉曲通流水,窗开绕画屏。晚烟千树紫,归雁数峰青。赖有双不借,深山劚茯苓”(同上)。几乎联联用典,然而不着痕迹,皆为我用,显出其学识与诗作的成熟。三兄弟中,曹鈖名气较大,交游也广。但其诗作,似不如他的兄长曹钊,更不如弟弟曹鋡。但也属英才。“边城柳色才垂绿,小院石榴已放红。”(《壬戌五月上回自辽阳驻跸丰润再过省亲志喜》)仿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一样清新可爱。在《雨中锦溪亭猎鱼》中,他的人生态度及审美情趣也得到了明显的展示:“戴笠寻山佳兴同,近山叆叇远菁葱。亭临浭水烟波上,人在秋光暮雨中。历历牛羊趋古渡,萧萧禾黍下西风。渔翁网罢倾樽酒,醉眼模糊天地空。”颇有些苍凉沉郁。《丰润县志》称他“尤精绘事”,部分作品收入了《国朝书画谱》。所绘制的《松茨写真图》最受时人珍爱,影响甚大,当时的大家尤侗、陈湖、沈荃、施闰章、王士祯、朱彝尊、纳兰性德、毛际可、顾景星、梅庚、高士奇、曹寅都在上面作了题跋,这在当时士林文坛中传为佳话。
未列入“三曹”的曹鋡,可能在乃兄成名时,他年龄尚小(他比他的大哥曹钊小20岁)。但后来居上,被认为是诗歌成就最高者。时人评论他“长于诗赋”。清代文学家邓孝威称赞他的诗“精、猛、奇、老”,尤侗说他的诗“体气高妙,有异人者。”对于“精猛奇老”中的那个“猛”字,我辈难体其妙,但“体气高妙”,倒是能体会得到,并觉得斯言不虚。《过唐恺庵遥黛山庄》中,诗人写道:“卜筑诛茅另一村,编篱插棘护柴门。年来渐识为农好,老去深知养拙尊。自拨新醅呼小妇,闲钞旧句课儿孙。春明更种南溪树,荷犁人归带月痕。”结句意象之美,把“为农好”、“养拙尊”诗性化了。曹鋡诗中佳句俯拾皆是:“儿童不识征徭苦,鸡犬犹耽自在眠”,令人震撼。此外,如“飞瀑欲兼双眼白,寒林忽坠一溪红”之奇丽;“远黛自能翻画谱,长松直欲上诗肩”之妙想;“潇洒红尘外,青山认寂寥”之洒脱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觉得他实在也不是浪得虚名。
除“四曹”外,曹氏家族中还有七人诗作入选,成一时之盛。但无非“载酒时相寻,敲诗只自记”。(曹牧《城西别墅》)皆属平平,兹不赘述。
曹氏诗外,有一人不能不提,那就是谷应泰。
谷应泰(1620—1690),字赓虞,别号霖苍,与曹鼎望同时代人。清顺治四年进士,曾任浙江提学佥事,诰授奉政大夫。主要著作有《筑益堂集》、《博物要览》和《明史纪事本末》。他不以诗名世,但在学术研究和治史上,古代丰润无出其右者。他有一首诗《子陵祠》:“荒祠薜荔枕名泉,百丈江声断岸前。白水有人容把钓,青山何意画凌烟。
鸟啼晓雾云中树,雨细春帆天际船。石蹬苔封难独上,依稀惟见客星悬。”放在别人那里,差不多是“犹吊遗踪一泫然”。在他这里,句句没离开写景,然而,写景中又句句没离开抒情。他的诗极少空发议论,含蓄丰满,令人回味,这就是他高明之处。在《上鹾台于侍御二首》中,他写道:“使君若问燕山月,故里枌榆尚未忘。”让人动容。“东风昨夜吹岩壑,万树横披尽素萼。疏影横斜月半昏,一声铁笛梅初落。”(《题画送钱黍谷年台应召大中丞入京》)这种送别之情,不著一字,却感觉沉重。可见他诗歌造诣之深了。
谁将赋笔写深愁
在丰润古代诗词创作中,我以为第一位词人也是最有成就的词人就是张纯修。
张纯修(1647—1706),字子安,号见阳。其祖父张廷榜,赠工部尚书;父张自德,巡抚河南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史。他由荫二品荫生任知县,后任庐州府知府。其墓志铭说他“以佳公子束发嗜学,博览坟典。为诗卓荦有奇气,旁及书法绘事,往往追踪古人。”张纯修与清代大词人纳兰性德诗词唱酬、书画鉴赏相交契,结为异姓兄弟。所著《语石轩词》一卷。
张纯修有一首《长相思·江行》,颇与纳兰相若:“山无清,水无情。只向征途管送迎。依然长短亭。 拟行行。重行行。江浪滔滔第几程。芦洲依旧青。”立意却与纳兰不同,虽有无奈,但无悲苦。平白如话,情蕴景中。他的词,格调时而高昂,时而低回,时而恬适,时而无奈,写尽其人彼时彼地所见所感,左右逢源,不拘一格。在《点绛唇·独夜寄友人》中,先是“独倚寒窗,衙斋无处无残破。挑灯且坐,留影陪我。”道尽了孤寂。词到结尾,“君知么,知心谁个?窗外峰如朵。”看似孤寂依然,但也翻出了峭拔。在写闲适中,也不乏落寞的那种复杂和微妙,他就能抓得住,写得出:“杏林几处花如织,朝来竟著寻山屐。满地落残红,难禁昨夜风。远沙平似镜,人在春波影。携酒坐花间,相看谁最闲。”(《菩萨蛮·看杏花和容若韵》)“一个词人即使没有伟大思想,也要有点真实感情,最不济也要有点锐敏感觉。”(《顾随诗词讲记》140页)我觉得,张纯修前者不足,后两者还是丰盈的。
据有资料说,张纯修与纳兰性德唱酬中,研求律吕,辨识宫商,渐谙词风词旨。清初著名诗人丁澎曾评价他:“今晋人选一代名词,以老眼次第阅之,当首推张襄平独得其法。后人可奉为科律。何辽海之多才也。”评价不为不高。张纯修又有诗稿,诗人毛际可曾为之作序,称其五七言、近体诸作“独抒心灵,萧疏淡远,如云之出岫,如水之下峡,如野鹤之警露,如孤猿之吟秋。”(见《安序堂文钞》卷七)用以评价其词作一样适用,惜其诗稿未能刊印,也不见流传于世。古人夸奖人,每每用这等妙语,让你去了悟,一如参禅。现举其诗一首,看是否如毛际可所言。“忽睹高寒月,松间照眼明。四围看郁茂,一隙认晶莹。都爱冰轮澈,便宜翠蓋横。涛声流万壑,露气宿三更。影射龙鳞密,波侵鹤梦惊。谷口留雅趣,疏荫寄深情。”
纳兰性德与张纯修唱和很多,可见二人性情、才识的相惜,更见二人的友谊和感情。当然,我们也可以读出他们之间的差异。王国维于有清一代,独推纳兰,谓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不是没有道理的。我觉得张纯修实在也逊纳兰一筹。随便从“诗抄”中拉出一首纳兰词,立分高下。
“城上清笳城下杵,秋尽离人,此际心偏苦;刀尺又催天又暮,一声吹冷蒹葭浦。
把酒留君君不住,莫被寒云,遮断君行处;行宿黄茅山店路,夕阳村社迎神鼓。”(纳兰性德《蝶恋花·散花楼送客》
这是纳兰性德于康熙十八年(1679),送张纯修赴湖南江华任上写的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