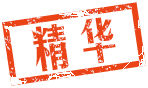|
|
不知为什么,幼年一些吃的喜好过了几十年慢慢消退直至殆尽,小时候不喜欢的,现今渐渐不再讨厌,甚至有了些期许和恋眷。那时,家里没人时自创一种奢侈吃法还遗在心里——撅几叶香菜,把酱油倒进碗,跑到橱柜前偷偷拔出香油瓶子的塞子滴上几滴香油在碗里,瓶口上的残油很馋人,而我,就用舌头舔干净。暖瓶里半热的水浇在碗里,一会儿,一碗闪着油花的汤就成了。把橱柜里的干馒头用手掰开倾在碗里,我去吃时满嘴面面的,而那碗汤才最美味。这些罗嗦的话,本就和今天想写没多大干系,那些年幼时记忆中久远的美味如今看来平常,它之所以美味,只是我顽固地回忆那些酸和流年地磋磨,继而让它们渗进骨里。而勾起我这么多琐碎思想的是年后打理冰箱发现的一瓶陈酱。
过旧历新年我清理冰箱,突然发现里面立着一瓶东西,把它从冰箱拿出才知道,原来是一瓶去年的陈酱。我连续用酱炒了好几次鸡蛋,味道酸还有些咸香。母亲听说后埋怨我:该吃就吃,今年新的也该好了,别省着。
每年还没出正月,父亲就开始赶集买上好的黄豆,等二月二龙抬头抑或阴历双日子做酱。母亲在闲暇时把豆子中的石粒和残豆挑出来,剩下的豆子滚滚的圆。母亲不这样做,做出来的酱如果咯了父亲的牙,父亲就会不高兴。
挑好的豆子还需用铁锅炒熟,炒豆不能用猛火,用我家后山上毛毛草当柴禾再合适不过了,不然豆子糊了也糊了酱。每当这时,我们哥仨都在锅边坐着,等豆子熟了,母亲铲一铲豆分给我们,熟过的豆子脆香。
磨豆子要跟宫奶家借小石磨把豆子一破两开,石磨用得久了,上面的刻痕变浅,磨出的豆子会有些碎。宫奶请老石匠把磨盘重敲了一遍,好用了些。前些天回家见到宫奶,她老人家脸上的皱纹和小石磨的磨痕揉在一起,不同的,磨痕越磨越浅,宫奶与父母亲额上的皱纹却越发深了。磨完豆母亲要用簸箕把豆皮簸掉,在当院油柔阳光下,飞起来的豆皮碰在阳光上,阳光一下碎成漫天零星,落在地上弄得一院子黄灿灿。
父亲把灶火点旺,烧一锅水煮豆。滚开的水,翻上翻下的豆瓣,母亲用勺子绞。这时,父亲填上能旺火的劈柴,满锅豆豉泛着泡滚,直到母亲用勺子舀一些豆豉,用手捻一下成了泥,然后让父亲停火。这当儿,父亲拔出灶火里的劈柴,锅里的豆豉也停止翻动。用来盛豆豉的小缸不过是卖酱腐乳的弃品。过去父亲不花钱就能得到一两个,母亲信不过它的卫生,每年做酱时,母亲旧时用洗衣粉、如今用洗涤灵里里外外把它刷上很多遍,直到漂洗的水没有丁点儿泡沫才罢手。
母亲讲,单日子敖豆,双日子做酱,她是听我太姥说该这样,延到现在。
关于酱引子,母亲说必须干净。过去酱引子是用些谷秕子放在炕头再撒上水,等到了开春,秕子上长一层绿毛,然后用碾子碾成沫子,老家管他们叫做“酱求”。我母亲做酱引子用的是过年间吃不完的蛋糕,等蛋糕在纸盒里有了些细细的绿色茸毛,再把蛋糕放在暖气上,茸毛长了些也就到了阴历二月间。不管父亲母亲谁有空,都会把酱引子掰开揉碎,如果宫奶家小磨有闲,再粉一下更好。
单日子熬的豆豉经过一夜凉了。回过天一早,母亲把粉好的酱引子倒进缸里,如果嫌新酱颜色不够好,母亲再熬些红豆,让色深一些。父亲用酱筢子不住闲儿绞,绞好以后,母亲洒上些盐,把一块白纱绷罩在缸口,用细线绳封好酱缸等新酱发开。
听母亲讲做酱方法有两种,一种发酱,一种打酱。发酱是盖上酱缸要等半个月,打开酱缸后酱的表面有一层膜,那是酱皮,可以和鸡蛋炒在一起味道很不错,不过我从没有尝过。我家是打酱,相对简单些——从做酱那天开始,每隔两天用酱筢子(用一根细长木棍,在粗的一端钉一块方木板),打酱时来回拖动酱筢子,有点儿像用水桶打井水的动作。两种酱都会在半个月后成熟,不过,不会有人做瞎酱(母亲说,必须蒸几个萝卜放在新酱里,要不新酱酸不起来。)
我家酱缸经年放在向阳的窗台下,每当父母亲掀开酱缸,看酱缸里面涌出的气泡,见酱缸表面的绒毛白绒绒。新酱还没有完全发好,父亲早就第一个评食,即便酸得差火候,他都会不住得吃。母亲无奈地说:咱家的酱最好吃的时候,酱缸也差不多见底了。
上星期回了家,母亲说:多吃点咱家的,外面做的我不放心,装酱的罐头瓶都洗干净了,你们回家吃不完就晒在阳台上,那东西晒不坏,别再留到过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