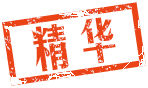|
岳母住院时,吃了几回馄饨,有西山口开滦医院北门对面的混沌侯,还有在凤凰道东北边一条小胡同里的千里香,吃过以后,觉得这些招牌虽然响亮,不过,虚名多了点儿。
馄饨侯的馄饨和千里香味道差不多,馄饨馅比千里香大一些。两者的馄饨皮薄得纸一样,被锅里的汤煮过以后,紧紧地贴在馄饨馅外,好像一个半高不高,半胖不胖女人,身上有一道道烫伤后留下的疤痕,还穿了一身大一点的的确良衣服,不小心落水以后又上了岸,衣服包在她身上,无数的褶皱都显露无疑,很难看。
就馅料而言,我不是很喜欢这两种馄饨,它们的馅料太绵细,吃在嘴里没有劲道,出溜一下划过舌头,余香停不住;馄饨皮几乎不用嚼,口腔里的唾液都可能把它融化。唯一值得提及的,倒是他们的汤料,很鲜香。说了这么多,没有半点贬低上面两种馄饨的意思,我感觉母亲包的馄饨要比它们好吃。
母亲做的馄饨最特点在于——馅大,皮厚,形状好看,最想说的,是那味道。
母亲通常会在晚上包馄饨,做好以后满满的一锅,连汤带水,很少蒸馒头和花卷,母亲说吃馄饨不用就着它们。馄饨又有肉又有面,还有汤,这么丰富的一锅足够吃了,父亲却不这么认为,经常埋怨没有干的,光吃馄饨吃不饱。
母亲不喜欢用热水和面,她说那样的面太软,包出来的馄饨没有咬劲儿。和好面以后,母亲用一块屉布盖在面团上,醒一醒。醒面的这段时间,母亲会掂对馄饨馅,馄饨馅基本上和饺子馅的内容差不多。肉要选五花肉,连瘦带肥一刀刀切成长条或者薄片,再用菜刀紧忙地剁,直到五花肉变成细细的肉粒。母亲喜欢用山葱当调味,碎碎的葱白搅进肉馅里,葱香味很浓。有时候母亲怕馄饨馅太腻会加上时令蔬菜,像白菜、冬瓜、有一次更特别,母亲把吃剩下的西瓜皮外面硬硬的绿皮削去,把剩下的白白的瓤剁碎掺进馄饨馅里,吃起来味道很清新。做好的馄饨馅得用力朝一个方向搅,边搅边往里面加水,加香油,搅好馄饨馅,母亲用筷子夹起一小团,舔一舔,尝尝味道。母亲这个超经典动作往往是失败的,因为母亲习惯最后才加盐,有时候忙乱了,盐和得不匀,时咸时淡。因为这些小事,父亲没少唠叨母亲,母亲一副爱谁谁的样子,再送上一句:下次你来。父亲嘴里唠叨,可等馄饨熟了以后,筷子往嘴里不停夹。
等面醒好了,母亲用擀面杖用力擀面团,边擀边用手往面饼上撒面粉,由于面团不是热水和的,硬一些,这时候父亲会过来帮忙。等面团变成薄薄的一张大饼,母亲像切面条时一样,把面饼来回折叠,一般折成五十厘米宽,用刀斜斜地切成菱形块。马上就要包馄饨了,母亲包馄饨是用筷子夹馅,把馄饨馅放在左手里的馄饨皮上,右手折叠混沌皮的两个角,用力把两片粘在一起,母亲不会把两个角重叠在一起,这两片粘好以后,再把另两个角折过来,也连在一起,像一只小猫脑袋,一个形状可爱的馄饨完工了。现在母亲年岁大了,开始偷懒,不再把面切成菱形块,而是把面搓成长条,像包饺子一样擀成剂子,不过剂子擀得长一些,包一个小小的饺子,用力抻长饺子,两个角折过来,做另一种圆圆的馄饨。
母亲包馄饨的时候,父亲经常边看边说:要是不用筷子,用饭店包馄饨的小抹子,多快,明天我给你做一个。这句话我听了快三十年,直到现在,母亲如今还是依然用筷子夹馅包馄饨,一点也不慢。
用来煮馄饨的汤,母亲不是很讲究。她并不炝锅,锅里放好水烧开以后,母亲手里拿着一棵白菜,一块块撕白菜梢,扔进锅里,再点几滴酱油,白菜梢在锅里滚,酱油星浮在水上,粘在锅沿。如果用菠菜点缀,就在馄饨出锅以前再放,不然菠菜煮老了很不好吃。母亲用一只手握着屏萜(用秸秆编成的圆形用来放饺子或者馄饨的东西)一手往锅里推馄饨,朝向锅沿的馄饨一个个滑进锅里,溅不出一点儿滚烫的汤。母亲拿一个铝勺子轻轻搅动,让馄饨一个个分开,这时候盖上锅盖,当汤再次烧开。锅里的汤顶着锅盖往上,母亲打开锅盖让泡沫落下去,加一点水,就像煮饺子一样。不过呢,水只能加一次,锅里的汤又一次翻滚后,母亲开始一下下搅动汤锅,不再让泡沫浮出来。母亲包的馄饨皮比较厚、馅大,得煮很长时间。煮馄饨时,来添乱的还是父亲,他唠唠叨叨,一会儿说,馄饨啊,皮子太厚,一会儿说,这哪是馄饨,简直是小饺子,非得这么大的馅儿啊。母亲不理他,一个人守着锅。
馄饨一个个飘上来,熟了,母亲撇上一小勺盐和味精,点香油、香菜,一碗碗盛给我们。
以前我家都是小细瓷碗,一碗可以盛四五个馄饨,一碗不够吃,两碗又吃不了。父亲就在集市上买了几个中碗,用来盛馄饨很合适。
吃母亲包的馄饨,需要用力咬开馄饨皮,面的力道在皮里,父亲和母亲的力量也在皮子里,柔韧。和饭店的相比,馄饨馅即便打了水,是少一些细滑,少一点儿水嫩,可肉馅有斩不断筋脉,比用机器挤压出的肉馅多了汁。牙齿咬开没有被切碎的肉块,溶于肉中的香味,比起所谓的名吃,香了很多。
母亲包的馄饨我们全家都喜欢吃,蛮香的,就是父亲爱挑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