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梁 平到万 县之间,过福禄坝,不进分水,有一条斜向左边的小路,那个地方,我只能用前后左右形容大体方位,因为一直弄不清东南西北----斜向左边的那条小路一直蜿蜒向上,过一座石桥,几丛竹林,颠簸不平的山路变成青石板路以后,就是三合监 狱。98年初,因为修建达万铁路,我们临时租住在监狱招待所,一栋三层青砖小楼。小搂地处狱区中段,背靠山坡,面临狱警家属区,算是热闹所在,饶是这样,我仍然觉得凄苦,每每被同学问及身在何处,皆答:在狱中。
可不是在狱中?立在小楼前边不大的空地上举目看,狱区四面青山如壁,杳杳苍苍,不远处,一条溪流从两山夹缝间泻下,叮叮淙淙,溪流两岸巨石如鼓,油菜花铺天盖地,馥郁腥甜,蜂缠蝶绕,给我北方人看来,就是十足的异域了。况且往来人迹寥寥,口音各色,我在川渝一带呆得久,重 庆或者成 都,广 安或者达 县,大 竹或者梁 平,其间微小的语调顿挫都辨得差不多,因觉抑郁。监狱修得早远,位置偏,交通闭塞,看起来寒伧破旧,我初去水土不服,又在怀孕,动辄天旋地转,不能自持,一连半个月都不能下楼,状态好些时候,才能勉强靠在阳台边晒晒太阳,面色苍白,像个人犯。
怀孕初期是那么渴睡,在狱中,没人打扰的情况下,我像一只缩在蛹里的虫,一睡就是一整天,早饭也不吃,午饭也不吃。工地上人员设备刚刚进场,我家男人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只有晚上才能得以一见,常常,他从工地上回来,见我虫子一样酣睡,非常发愁,又不能呵斥,又不能指责,只得好言相劝,甚至生拉硬拽,迫我起来,喝一碗米汤,然后拉着手去散步。初春的夜晚,风还很凉,路两边是丛生的芭蕉,我们顺着蜿蜒的青石小路往监狱深处走,半小时后到达真正的狱舍,一座壁垒森严的青砖建筑,高墙铁网,步步为营,路灯昏黄,风吹来,背上生出冷冷的鸡皮疙瘩,我抓起他的手,不由分说,返身便跑。
监狱寒伧陈旧的环境,需得大浓大厚的春色衬托,才见明媚。所以人间四五月的暮春,在监狱,方是春的开始。祛了山间寒气,风也变得绵长酥软,整天薄云丽日,少见阴霾。孕初反应过去,我的胃口仍不见好,但是终于不像原来那样整日恹恹,每天上午处理完手头工作,便搬一张藤椅出去,坐在阳台上吹风。不知什么时候,两只燕子在我们屋檐下筑了个巢,安心地孵一窝小燕子,像是来陪我。常常,孕着新生命的两个母亲沐在阳光下,闻着山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非常安详。那年,我们隔壁住着一对沧州夫妇,也是新婚,然而整日争吵,温馨全无,于是,春天在他们家屋檐下安排了一窝马蜂,两人想尽办法,驱且赶之,泥糊,火烧,棒捣,均不见效,蜂巢越来越大,越来越壮观。春天真是有灵性的季节。
在监狱,每天早上,我还在迷糊的睡中,楼下空地上就聚集了附近的山民,拿着自家栽种的蔬菜来卖,或者鸡蛋,做最简单的交易。那时候食堂饭菜不好,我们买了一只电饭煲开小灶,蒸得最多的就是鸡蛋羹。山里的土鸡蛋是真正的绿色食品,我仍然吃不出味道,经常趁他不注意,偷偷倒掉。我最爱趴在阳台上,看他买鸡蛋的背影,蹲在老农摊前,一只一只挑选,五月清晨的阳光从树枝的缝隙中漏下来,洒在他身上,那么灵动。白天,男人们都去了工地,女人又寥寥无几,整栋小楼基本上是空的。精神好的时候,我就去外面转悠,顺便买一些零嘴。监狱只有一条青石板路,两边的店铺非常陈旧,有一个小饭店,一个理发店,一个零售铺,一个修车铺,一个热水房。狱区活动着一些快刑满释放的犯人,比如靠着修车铺的理发店,理发师傅就是一个盗窃犯,差六个月服刑期满,就可以出狱了,因为不值得逃----逃的话,追回来是要加刑的,所以安安心心经营着理发店。他的面相看着也老实,然而第一次听到,我还是吓了一跳,觉得头皮发麻,差点儿扔下理了一半的脑袋跑出去。后来就不再去那里理发,宁可头发荒芜着。打开水也是,每次我拎两只暖瓶去热水房,烧锅炉那个犯人都放下手头的铁锨,跑去帮我开门,我看他一眼,贴着门边儿走进去,谢谢也不说一声。心魔是个很厉害的东西。
监狱的伙食乏善可陈,平常吃得最多的就是莴笋,川渝百姓对于莴笋的感情,像北方人之于白菜,亲切入微。素炒莴笋片,肉炒莴笋丝,排骨烧莴笋块,清炒莴笋叶子,莴笋的须须尾尾都不浪费,一直到现在,我都不能看见莴笋,恨之入骨的感觉。我想吃酸白菜,醋溜土豆丝,萝卜蒸饺,西红柿炒蛋,甚至腊肉炒荷兰豆,----那简直是奢望了,都吃不到。到夏天,天气炎热,情绪焦躁,我几乎日日对着莴笋垂泪。有时候去楼下小饭店改善伙食,也没什么新鲜花样,但是可以吃到鱼和砂锅土鸡,运气好的话,还能吃到河蟹,橡皮擦大小的河蟹对切成两半,搁上辣椒姜片花椒大料上灶猛炒,很好吃。有一次还吃了几块蛇肉,----当时并不知情,全当鸡肉咽下去,蛇汤也当鸡汤喝下去,并无异味,事后被人告知,一阵呕。饭店老板娘和我差不多年纪,当地人,也是孕妇,老板----他男人,据说是从这所监狱出来的劳改犯,从前做贩卖人口生意,监外执行那几个月,男人使出几年不用的本领,就近给自己贩了个老婆,从此在监狱落地生根,并且开花结果。他们的爱情应该很曲折,或许曾经电光火石、天崩地裂,我想,但是连他们自己都嘿嘿一笑,大概觉得滑稽又自卑,我就不好意思张口再问。----老板娘见我欲把蛇肉呕出来,赶紧跑过来阻止,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孕妇吃蛇肉,生出的孩子就不会长疮。我到底没吐出来。
那年夏天,天气大热且旱,连续一个月不见落雨,山泉断流,靠天蓄水的监狱几乎陷入绝境,最紧张的时候,吃水都成了困难。饭店小老板从半山腰仅有的一眼清泉挑水过来,卖给我们,每担两块钱。这个苦活计,连监外执行的犯人都不愿意做,只有他做得热情。每天傍晚,他弓着筋骨条条的腰,像一只佝偻的虾,往每间屋子送一担水,再从大伙儿手里接过两块钱硬币,扯过肩头的毛巾擦汗,一边憨厚地笑,露出一口白牙。他的女人靠在小饭店门口,腆着肚子,看着他一趟一趟来往。天气是那么热,风扇没日没夜无助地转着,因为缺水,每天,我只能用湿毛巾擦擦身上。我又恢复到孕初的状态,白天恹恹不起,并且抓紧一切可能的空隙跟他哭泣,------他实在是忙。大热那几天,屋子里没法儿待,傍晚,人们纷纷下到山脚下的溪流里,找块石头坐下,脚泡在溪水里消暑。溪流很深,基本上能算做山涧,稍稍开阔的地方被年深日久的流水冲出一个潭,当地人叫做龙潭,夜色下泛着幽绿的光。八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们照例在溪水里乘凉,男人们在不远处的龙潭里洗澡,一阵风从山谷里蓦地杀出来,紧促又阴冷,一刹间吹得我胳膊发麻。我又跟他哭起来,冷,要回家。
他疑惑地问,你冷?
我冷。我几乎哆嗦着爬上岸,又一口气攀上几十米高的坡坢,回到人境。第二天早饭时听人说,龙潭里昨晚溺死了一个男人,是个刚毕业的狱警,二十岁,前天才报道。我扔下筷子跑回屋。一连好几天,我躲在屋子里,紧闭门窗,还是冷。----小伙子溺水那一刻,肯定向人求救来着吧?是不是那阵风?他已经张不了嘴,风就是他的信号了,他弄出那么大的动静,都没人察觉,他肯定死得特别的不甘心吧,肯定的。那两天,监狱上空笼罩着一股悲凉,人人都在议论这件事,我一声也不敢吭,怕给人窥破了心事。两天后又有消息传出来,说死者家属来,只领走了抚恤金和丧葬费,拒绝领回尸体,按当地的风俗,横死的孤魂野鬼是不能入祖坟的。小伙子被埋在山脚底一颗芭蕉树下,不大的一个土堆。我后来去采了一些野花,搁在土堆上。天气顺势凉下来,开始下雨,没人再去龙潭。
熬过一个溽暑,初秋我回老家待产,后来又调换工作,从此再没踏过那个地方。那段狱中岁月,就像一块补丁,缝在我不长的人生旅途中,想抚,却总也抚不平。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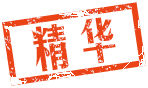
 匿名
发表于 2012-3-25 00:45
| 来自河北
匿名
发表于 2012-3-25 00:45
| 来自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