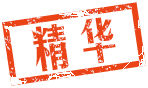-
胖仔米线在新区开业时我没赶上,后来去补吃了一回,一大海碗排骨米线加一个酱肉金饼。米线做得精致,海带丝与咸菜丁铺底,清汤绿叶,亮晶晶一层油花漂在上面,色香味俱全,就是怎么吃都找不着感觉。
我印象里,米线不是这种郑重其事的小吃,它应该在低窄阴暗的雨棚下,或者露天的集市中,有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锅,一个不甚整洁的少妇,散着发髻,背篼背一个熟睡的孩子。她挽一截粉丝一样的米线投到滚水中,筷子左右一搅,旋即捞起,浇上事先炖好的汤汁肉料,唏嘘着端给客人,——她的拇指或许还浸在汤里,然而整碗米线都是她做的,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2002年深秋的天气就是这样,我在晚上看书,凌晨睡去,早起散步到华光农贸市场,花一块五毛钱吃一碗白水米线,两个小笼包,出门再买一份报纸,有时候是几束鲜花。小店位置好,一天人流不断,早起卸下铺板支出帆布就是个早点摊,半前晌收起小摊经营米饭炒菜,晚上改卖酸萝卜老鸭汤。店主面色黎黑,戴筷子粗的金项链,绿宝石戒指,边抽雪茄边靠在门框上收钱,神情寂寞。周围的长嘴妇说,他是个忘恩负义的男人。
立冬后不久,小店老板娘上了吊,发丧时店主请了戏班子,与麻将席搭起一大片,锣鼓铿锵,麻将声声,所有人都在庆祝她的识相。我立在阳台上跟人发短信,说,亲戚不见悲,他人亦已歌。一会儿收到回复,说,悲莫悲兮生别离,惟愿此生常相知。
那个夜晚,路边矮草稞里燃着白蜡烛,风里一飘一忽,像不甘的魂灵,生冷,清寂。我依然去那个店吃米线,店主依然靠在门框上收钱,新继位的老板娘神态婀娜,睇睨含笑,擦口红,烫碎发,描眉,画眼,抽烟,符合我心目中一切坏女人的装扮。
这个礼拜以来也一直在吃米线,陕北小店,一碗米线做得热闹无比,红油,麻椒,海带,葱花,豆腐丝,芝麻,碎米花生,琳琅满目,叫人吃得新鲜而惊奇。但是从前天晚上开始,我胃疼,周身低热乏力,拒绝米线、面条、包子、馒头、烙饼及一切吃进肚后才开始发酵的面食,我的胃细微而酸楚地抽搐着,迫切想吃一点米饭和炒菜,或者一碗粥,几根咸菜。我是这么迅速地抛弃了曾经的热爱,并且不能想象它的味道,像一个由爱情堕入柴米油盐的俗妇,原先的美好靠时空距离维持着,一旦得了手,爱情不过是应嘴的零食而已。
昨日大风,傍晚初歇,我在肮脏偏僻的小镇上从东找到西,逢店必进,逢人必问,——有米饭和炒菜么?我找不到一家卖米饭的小店,这个晋南小镇的居民,他们吃面条,面筋,面疙瘩,饸饹,水饺、夹肉馍、蘸尖、帽盒、石子饼,他们把蒸馍掰开泡羊汤,把饼切碎焖成丝,很多天都不吃一颗米粒。路边的民房透出温暖的灯光,像黑夜里温柔的眼睛,有几分钟时间,我把手揣在兜里,迎着风,寂寞得想掉泪。
——我总是在喧嚣之后才想起一些被时光与地域抹去的东西,永远地顾此失彼,又永远地不合实宜。在一家饺子馆吃番茄炒蛋时,喘息不定的风又渐渐刮起来,扬起漫天沙尘,象簌簌落下的雨,隔着风沙往回看,那一刻,许多人事,似是在旧时光里淡去了,怎么我,却放不下一碗白米线的清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