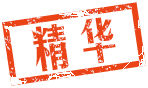|
过年 工作原因,我不一定能在家过年,侥幸的是这几年都赶上呆在家里了。如今年味越来越淡,旧节日明显干不过洋节日,当然过年除外。人们流动的空间和时间越来越久远,漂泊感让人在这个借口下酝酿出浓浓的回家的期待。每接近年底,我们掰着指头算计今年能不能赶上在家,赶上了心花怒放,赶不上便自我安慰:过年也越来越没意思了。过年也的确越来越没意思了。无论我们怎么挽留和营造也没了小时候的味道。 从前过年好像是一个时间段的节日。一进腊月,年的味道就扑面而来了,虽说正是数九寒冬,却好像春风已经在不远处整装待发埋伏好了一般。煮腊八粥,扫房,杀猪杀鸡,烫猪头羊头,煮下水,煮肉,预备炮竹。这些虽然没我们小孩子什么事,但看到大人们忙忙碌碌,偶尔也能让我们打打下手,心里面就按捺不住地兴奋起来。更让人兴奋的是忙碌小孩子自己的事。忙着被大人量尺寸做新衣服,忙着从厢房的角落里找出满是尘土的旧灯笼,掸掉尘土,糊上新的毛头纸,要是能得到一个猪尿泡就更好了。忙着收集旧笤帚炊帚,正月十五扔火球要用。腊月二十八二十九,家家的大锅里面就开始煮肉了。灶火坑儿填进了老树根糟木头,堂屋里热气腾腾,房顶上的烟筒冒着青烟,肉香满村子都是,我们眼巴巴地站在锅台前,闻着肉香,口水在嘴里不停地涌动。终于煮熟了大块的肉坯子,大人们用炊帚往上面抹糖色,看我们眼馋的样子,会撕下小块的瘦肉,蘸点酱油塞进我们嘴里,鼓着腮帮子,我们满足地跑到当街找小伙伴们炫耀去了。过年那天我们一反常态地不再睡懒觉,早早爬起来,穿新衣服,放炮竹,给老人拜年,要压岁钱,要炒花生炒瓜子,要糖疙瘩,新衣服的口袋胀得鼓鼓的。中午吃完好饭,就急切地盼望着天黑,太阳刚刚落山,天还蒙蒙亮着,我们已点起了灯笼里面的洋蜡走上街头巡游了。街上有了星星点点的灯笼,渐渐地多起来。天黑下来,满街就都是高低拥挤的灯笼了,人们走不开,只能排着队迤逦着前行。当然并不会一直这样秩序井然。有人会故意在后面往前拥,突然地往前拥,前面的人没准备,难免就摔倒在地上,一堆人噼里扑噜跌在一起,好多纸糊的灯笼烧起来,有人大哭,有人大笑。还有人走着走着,偷偷点燃一个小洋鞭迅速扔进别人的灯笼里面,啪的一声,灯笼就着了,不着的灯笼也会被炸得百孔千疮,或者手里抓一把土,噗地撒进别人的灯笼里,一下把蜡烛给砸灭了。我和邻居家的男孩还曾经偷偷在街上拉起一条绳子,横贯在当街的道上,人多的时候突然拉起来,绊倒了一大群人,烧了一大堆灯笼。夜深了,我们打着哈欠回家,有的人灯笼亮着,有的人灯笼暗着,,有的人的灯笼就只剩下了铁丝编的架子。打灯笼可以打到初五,之后大人们就不允许了,因为平常日子,只有死人了才打灯笼。正月里开始串亲戚,当然是大人的事,小孩子们就是跟着去亲戚家接着吃好饭。一辆破洋车子驮了一家人,小孩子偏坐在前面的大梁上,车把上吊着点心和酒,颠簸在乡间土路上,来来往往,到处都是这样的风景。串完亲戚差不多也该十五十六了,晚上煮元宵,吃完元宵,到村外的麦田里扔火球。用过的秃笤帚点了火,用力的抡起来,再扔到天上,起起落落,满地里都是。火球烧完了,就和邻村开坷垃仗,我们村和北面的麦坡打的时候最多,麦坡领头的还是我的堂表兄,阵地大多在我们村北面遗弃的老砖瓦窑一带。有一次我们大胜,一直把他们打到了麦坡村的北面,我们还缴获了战利品,一把洋火枪,一个弹弓子。 后来生活条件渐渐好起来,有了春晚,有了电视,有了许多花花绿绿晃人眼的东西,过年却越来越没了意思。新样式的塑料的,彩纸的灯笼渐渐替代了自己做的丑陋的灯笼,它们高挂在楼檐上,商场里,摇曳在霓虹的背景上,年夜里的灯笼却慢慢少了,少了,稀稀落落的。再后来,老家的年夜,街上漆黑一片,再也看不见一个灯笼穿过长长寂寞的街道。电灯电视虽然照亮了每一家每一个屋子,空气里却闻不到了洋蜡烧起来淡淡的蜡油的味道。 娱乐匮乏时,我们的童年到处都是欢乐,在每一个门前街角,田间地头。物质丰富了,我们却失去了味觉,即便现在星级酒店的大菜,美则美矣,却也实在美的琐碎间接,太多调料扰动着我们的味蕾,磨灭了我们曾经因为清贫清淡而敏感热切的味觉,我们因此而挑剔而麻木慵懒。小时候,清水煮瘦肉蘸一点散装酱油的味道是那样朴素直接并且顽强地穿越这么多年,依然勾引着我舌底的津液。仅此而已,有些东西似乎不可逆转,比如人生情境,只能让我们徒劳地怀旧。 上学时,每年过年那天的下午,我们一群打篮球的玩伴是在麻山寺的兵营里度过的,和解放军的一场友谊赛激烈热闹。黄昏时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家,脑子里还回想着每一个得意的假动作和漂亮的上篮。上班了,成家了,年龄大起来,也不知道从哪一年起,这一切也都渐渐远去。玩伴们各自鸟兽散,大都没了联系,记忆里只留下年轻却模糊的容颜。人生有许多年龄段,每一段,会有不同的人群陪我们一起走过,风流云散时,我们却不曾察觉,连一声再见都不曾说过。再后来是和邻村几个依然年年聚会的初中同学象征性地爬爬村北的小山。开始时是一对对小夫妻,再后来,带上了小孩子。今年,突然发觉孩子们都已到了我们曾经年少轻狂的年纪了,男孩子高大英挺,女孩子们也个个开放的花一般。青春真好,尽管我们各自的青春因年代差异而有所不同。我也总会在女儿些许的任性叛逆中寻找自己执拗轻狂的背影。 天涯芳草碧茵茵,无复追风与绝尘,一转眼间就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前的事了,却好像都在昨天,而我们,再也不是从前的追风少年。《世说新语》载: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流光抛人,一世枭雄尚且如此,我们这些春荣秋枯的营营俗子,更不知道一茬一茬地老去了多少。老家的山,那些坡坡坎坎,却几乎都还是从前的样子,和老爸谈起时,老爸也会说,我小的时候爬到哪座山哪座山去玩过,哪里有坍了的破庙,那里有山泉和老井。 2012、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