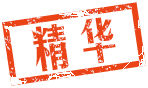|
姨妹 我在一个小山村开着个小书店,经营惨淡,勉强维持。一日来一妇女,领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买书。女孩挑书,我们在一边唠嗑儿。闲谈中我得知她们家很穷,但孩子在学习上的花销,家里从不算计。那天孩子挑了一大堆书,妈妈看了看,自言自语说,好像没带那么多钱,问我可以便宜些不。我算了算,按本给她,也得一百多。她便回家借来了五十块钱,给孩子把书买走了。在这个穷山恶水的地方,肯花一百多块钱给孩子买书的家长,可说凤毛麟角。 大约过了两个月,一次,一个小女孩挑了一本作文书,问我可以优惠不。“我好像应该叫你大姨夫吧?”那孩子很会说话,“我妈和你们家有亲戚,我妈是北王庄的。前些日子,我妈从这买了一百多块钱的书呢。”她一说我还真想起有这么回事,对象和我说过,有一个姨妹在这里。姨妹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子,因为家里穷,父母窝窝囊囊,村里人瞧不起,所以哥哥小三十了,也没混上个媳妇。父母为这事整日唉声叹气,愁眉不展。正好这里也有一户人家,情况大致相同。于是有人撮合,两家换亲。起初姨妹是不情愿的,但为了哥哥,为了父母,为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她委曲求全答应了。 “大姨夫,你想起来了吧?”孩子问我。 “哦,是的。我给你算算。” 最后,她又以最优惠的保本价拿走了。可没料到,不过一小时的时间,她又来退书。退书可以,我忍无可忍的是,她要求我按定价退。 “那怎么行?不挣钱,到家到业。退货我如数退款,这都可以。怎么能让我赔钱退书呢?”我难以接受。 “要不那样行不行?大姨夫你帮我个忙。”看那孩子战战兢兢,我点头。 “我妈要是来问你,你就说我花定价买的。我想退,你不肯,行不行?” “合计着,我赔了夫人又折兵,你偷走驴我拔蹶子。低价卖你书,还让我背一个黑心商人的黑锅。你妈还得说我六亲不认,钻钱眼里了。”我苦笑着。 “好哇,我就知道你个小死丫子没说实话!”说着话,一女子气势汹汹闯进来,我一看,是姨妹。 我没来得及说啥,孩子已经吓得缩到墙角了。 “姐夫,我告诉你,甭给她脸。”姨妹气得喘不过气来,“你给我说,你跟你爷要那十块钱到底干啥使了,今儿你不给我说清楚,看我不扒了你的皮!” 那孩子吓得哆里哆嗦,哭声阵阵。 “你给我止住!”妈妈一声令下,女孩子果然不再抽泣。 “老实说,你是不是买用不着的了?买啥了?” “买吃的了。一根辣条,一个口喷。。。”孩子断断续续地小声说。 “甭说了。告诉你,下个月的零花钱一分不给了!”妈妈大声训斥,连我都大气不敢出。原来孩子从爷爷那要了十元钱,说买书,其实买吃的了。为了堵妈妈的嘴,她又从我这里买了本便宜书。谁知,孩子的事哪里瞒得了妈!妈妈一听就来了气,说这里的书店作文书从没有卖定价的。让她把十块钱下也得给下出来。 一切平息了,我劝姨妹说,可以给孩子讲讲道理,毕竟那是个孩子。她说,她没文化,性子急,不会讲道理,一说就气得上气不接下气,就想动手。她说,孩子到了家就会看动画片,除此外就是琢磨着要钱买吃的、玩的,这样的孩子将来肯定不会有出息。现在又加上说瞎话,更是不可饶恕。虽说觉得妈妈有些凶,但想想现在的孩子,想想这个孩子的所作所为,也情有可原,甚至可以说,是个很难得的好妈妈。 接下来的一件事,却让我对这个大字不识、脾气暴躁的姨妹肃然起敬。 姨妹有个小女儿,六岁了。有一次回妈家的时候,孩子感冒了,她带着孩子到村里的大夫家打针。医生是个新手,女的。量了体温,医生说打一针吧。没想到,针刚扎下去,孩子就声嘶力竭地拼命哭闹,说右边脚疼。一看右脚,脚趾向下耷拉着,脚后跟使不上劲。大夫一看也慌了,赶紧骑上车子,到镇上的医院看,医院说看不了,让去县医院。到了县里,还是不行,建议去市里的儿童医院。可她们口袋里都没装多少钱。大夫说,让她等一会,她回家里拿钱。 过了好长时间,却是姑爷带着丈母娘来了——大夫的妈。坏事就坏在这个妈身上了。要不怎么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妈妈一下自行车就面沉似水,大吵大闹:“咋的?镇里看了没病,县里看了没病,又想上市里?想的倒美!没病就没病,想讹人啊?告诉你,一分钱没有,有法儿你使去!”老太太说完,撇下这娘俩,带着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喘着粗气走了。 姨妹气得说不出话来,只好返回家中,拿了钱去医院。她先后在市里和北京两家医院给孩子看病,他们一致认为是坐骨神经损伤,大夫打针所致,万幸的是,伤到的是副神经。贫贱夫妻百事哀,因为穷,每前行一小步就有想象不到的困难。就说住宿吧,孩子治病的钱还不知够不够用,就只好委屈自己,能将就就将就了。她或者在大街上某处露宿,或者在急诊室租一把躺椅对付一夜。在医院和车站之间,能自己抱着孩子走,能坐公交,就绝不打的。吃的管饱不管好,喝的就是白开水。治疗一段时间后,孩子的病情总算有了好转,就转到县中医医院在穴位上扎针,针灸治疗,一天一次。姨妹家里在县城最北边,离城里五十多里地,坐公交车往返也得十块,家里难以承受,就只好她用自行车带着孩子去。每次到医院,从孩子的屁股到脚跟都要扎上一溜针,孩子一声不吭,告诉妈妈说不疼,可妈妈却每次都哭得泪人似的。一年半以后,孩子逐渐恢复,这时才顾得上去找当初打针的大夫交涉。想不到,老太太竟然反咬一口:“这是穷疯了,见谁就想敲一杠子。你想做泥腿子不是?想讹我们,告诉你,门儿都没有!钱我们一分没有,有能耐你们随便使去。” 姨妹气得几乎晕倒。自己孩子受了罪,欠了一屁股债,家里的地也荒了,遭受精神物质上的双重打击之后,还要面对这黑白颠倒的残酷现实,还要背上泥腿子、敲竹杠的恶名!姨妹气得一口饭也吃不下去,夜里合不上眼,第二天就到法院告那大夫去了。法院说,要把病治好以后,确认是医疗事故后,才能打官司。于是,她又一次次跑北京,到市里,开证明、做鉴定,自己都不知跑了多少次,光路费就用去三千多,终于有了些眉目。 但这回却有了另外的阻力:丈夫不爱烦了。劝她别闹了:“咱没人,又没钱,打啥官司啊。你少听说了,冤死不告状?何况你又是一个妇道人家。就算赢了,能赔多少?要是输了呢?人家早把上上下下打点好了,人家宁可把钱花在送礼上,也不会给你。你告不赢,好好过日子吧。”在他看来,姨妹此举无疑是蚍蜉撼大树,没有好结果。 她一听也急了:“我非把她整倒,就不信他这个劲儿。我孩子受那么大罪,我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气,就这么窝窝囊囊地暗气暗憋了?我咽不下这口气!你不愿意出头我自己去。” “那得花钱,傻娘们儿!” “不行。没钱?好办。你不是没钱吗?明儿去村支部,上大喇叭里喊去,谁帮我打官司跟谁去。” 丈夫气得不说话了。 其实案情并不复杂,证据也好找。问题是,一来如今求人办事难,没人可求就更是难上加难,倘若再没有钱呢?困难可想而知。有时看去很简单的事,举手之劳,办起来却难于上青天,微妙啊。个中奥妙办过的人就会知道。二来呢,大夫家也就是抓住了她们家没钱没权,没气没囊,逆来顺受,几辈子都这样,村里没人瞧得起她们家。一个个烟不出火不进,怕事,没原则地忍。姨妹一妇道人家,整得出啥? 可这次还真就碰上个认死理、不服输的。她觉得法院毕竟是人民法院,这社会还没到颠倒黑白的地步。一次不行两次,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公道还是有的,好人也从来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法院终于给了她一个公正的判决:属于医疗事故,赔偿经济损失三万二千元。 大夫家一看要坏事,就想转移财产,他们搬到一个又矮又破的小房子里住。而后便以家里没钱为由,不执行判决。她只好又找到法院,要求强制执行。 最终把那个大夫送进了看守所。她们家里也软了,说准备出一万七千块钱,后加到一万九,她坚决不答应。在法官调解下,最终得到二万三千元。连治病,带告状,还搭进去两千,别的还不算。但她要出的是这口气。 都这个时候了,那老太太还是嘴硬:“算我们倒霉,讹去的钱不好花,谁让我们碰上个滚刀肉呢?” 那个大夫,不仅是赔了些钱,实际损失无法估算,因为她没有行医资格了。即便再干,也没人敢找她了。嗨,倘若当初不耍赖,积极稳妥处理好事情,结果恐怕不会这么惨。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可是,现在说这些都晚了。 世上没有后悔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