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山城
作者:谭忠惠 发帖:波涛 来源:滦河网【燕北文史】
海纳百川,耳听八方。历代当政者都应虚怀若谷,听听过来人的倾诉,或对或错,都于治世有益。所以,真的希望能有更多的老同志能像谭老师这样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留给后人们。 1.在“四清”最后的日子
1966年,当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的时候,我们还在唐山的滨海地区乐亭县曹庄子人民公社,开展以“四清”(最初叫清财务、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唇,后来叫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时候,采取混合编队大兵团作战的方法,我们是地区总团下设的一个分团,人员大多来自唐秦两市和迁西、迁安、滦县等县的干部,有一百多人,还有解放军两个团参加“四清“的几十名军官。到这年秋天,文化大革命吃紧了,分团中的县级领导干部都集中到市里去了,我原是分团的政治部主任,被总团任命为副政委,随即为分团党委书记、代政委。其实我那时只不过是迁西县委组织部的一名干事,这也是应了那句话了,“山中无老虎,猴子成大王。”不过我那时虽然比较年轻,也是个扎扎实实做事的。
领导干部都走了,留下了一个摊子。此时,大部分村已经完成了“阶级复议”和“清理财务”等工作,以后的任务主要是进行整党和班子建设,我们要在领导不在的情况下,抓紧时间,把余下的工作做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大革命的声浪逼近,不时有情况传来,说在县城和临近的乡镇,红卫兵破“四旧”,把字画都烧了,把花盆儿也打碎了。这些情况传到曹庄子,有些小学高年级的学生也提出破”四旧”和张贴大字报,也有的大中学生回家来,传布城市里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这些情况引起了我们的重视。那时中央发到县级的文件,也发到分团,我们对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也进行过学习,但是对红卫兵的过火行为也不甚理解,也感到对群众运动也有个引导问题,因此,我们部署对破“四旧”要分清旧与非旧的界限,指出农村中买卖婚姻、封建迷信、赌博等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才是“四旧”,应大力破除;对花卉和字画等文化艺术品,都不应视为“四旧”加以损坏。对学生要写大字报的,要告诉他们,他们年纪还小,而写大字报又浪费纸张,可以引导他们写小字报,在教室和校园内搞墙报。对回家的大中学生,工作队要主动接触,并听取 他们的意见,而且要善意的告诉他们,因为他们长期不在家,对村里的情况不大清楚,不经过调查研究,不要轻意地表态,这样对他们对工作都有好处。这些话是我在全体队员会上讲的,那时候也许是全无顾忌,所以过后有的同志对我说:“别人不敢讲的,你都讲了。”但是我认为我这么说并没有什么不对,而且我们这样做了,也收到了一定效果。客观上,曹庄子没有一所中学,而且地处滨海,也许是天高皇帝远吧,尽管城市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热火朝天,这里却相对的比较平静,因此,也使我们争取了时间,得以集中精力开展工作。可是好景不长,在进入冬季以后,大约在十一月份,部队的同志就撤走了,此时我们也有了一种预感,在具体分析了各村的情况以后,决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抓后进促平衡上,帮助工作进度慢的队解决矛盾,清除障碍,促进工作的开展,对面上的工作,则强调在搞好班子建设的同时,解决好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和有争议的问题,为工作队的顺利撤离创造条件。 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越来越紧了,我到总团开会时,己经看到有些红卫兵聚集在总团的门前,纠缠不休,总团的副政委刘任英在工作人员的维护下,与红卫兵对话,我感到有什么情况就要发生似的。我们在继续抓紧后期工作,同时又满腹狐疑的观望着一个不可知的局势。终于有一天,分团的李团长(开滦唐山矿的办公室主任)和政治处的张主任(秦皇岛市某区委千部)急匆匆地走来神色慌张地对我说;“邻近的分团己经撤了,我们也快撤吧,晚了就走不脱了。”我听了以后,最初的反应是感到突然,我原来也曾想到哪一天会撤退,但是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可是我们也不能这样抽身就走哇,我告诉李团长和张主任:“我们要善始善终,再多站一天,布置各工作队召开党员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座谈会,做好善后工作,并与总团联系,准备好撤退的车辆。”此时各村的领导班子都己建好,我们已基本完成了任务。 2.撤退时仓促而有序
1966年12月29日清晨,有几部卡车驶进了团部后边的场院,我和李团长站在习习的寒风中,迎候着各工作队的到来,我们有点担心,生怕那个工作队遇到麻烦撤不出来,直到最后一个工作队到齐了,我们才‘放下心来。我简单地致词,向同志们告别,先送走了唐秦两市和其他县的同志,而后带领迁西的几十名同志,分乘两部卡车返回迁西。
汽车驶出乐亭县境,沿铁路线西行,经过古冶,然后向北驶去,穿过山野,越过村庄,一路上没有人说话,大家都沉默着。这使我想起两年前我们乘车奔赴“四清”前线的情景,那时候,大家斗志昂扬,一路高歌,像是开赴一个光荣的战场。而今却是另一番心情了,我们像一群从订线败退的士兵,拖着疲惫的身躯,从战场上撤下来了。“不,我们没有败退。”我这么想:“两年来,我们遵照党勺指示,在“四清”前线转战两三个县,通过艰苦的工作,完成了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没有理由自责。”想到这里,也就平静了许多。汽车继续沿公路奔驰,车后扬起尘沙,最后风尘仆仆,也驶进了迁西县城,驶进了县委大院。人们纷纷下车,忙录着往下卸行李。我告诉大家:“先回家或回各自的单位吧。”人们又纷纷背起行李卷儿,提着兜子,向大门外走去了。
我望着那些年青的“借调干部”的背影,不由有些伤,两年来,这些男女青年日夜和我们战斗在一起,每月只二项30元的生活费,无怨无悔,很是令人钦佩的。他们是由农讨选拔的优秀青年,本是怀着美好的憧憬和理想,投身于“四清”工作的,如今又带着他们的梦,悄然地回到农村去了。望着他们的背影,我还真的有些无奈而又无限的感喟了。我送走了同志们,转身和迎面的同志打过招呼,直奔县委组织部,这是我的工作部门。我一进办公室,陈俊英同志就立起身,满面含笑地迎上来,几句寒暄后,她告诉我朱部长调市里了,樊副部长调商业局了,郭副部长回原籍了,张甲调党校了,搞“四清”的还没回来,现在部里只有她和张启兴、李景禄三个人了。而后又说:“上边有指示,把个人携带的枪都收上来。”这我理解,我们党历次运动都是这样的,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搞运动就要整人,难免有人想不开。我把我随身携带的德式三号手枪和几粒子弹交给了她。在“四清”前线,一位部队的团长送给我十几粒“五四式”手枪子弹(口径与德枪是一样的),这不是组织上发的,我留下了。这后来差点成了我私藏弹药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证,幸好我说的有根有据,他们才不再追究。当然子弹是没收了,而那只手枪也永远没有回到我的手中。 县委大院,冷冷清清,见不到先前那么多人—后来才知道,当时县委领导们大多还滞留在市里,自“文革”以来,有些同志也被安排到下边去了。我没有向陈俊英过多的询问,就与她告别,扛起行李卷儿回家了。 3.走进“文革”
我从“四清”前线回来,在家休整了一天,也就是洗洗澡,理理发,换换衣裳,没有顾得过问家里的事,也没有帮助家里干点什么,就急着返回机关。妻子说:“你走了两年多刚回来,还不在家休息几天。”我说:“不了,我还不知道机关的情况呢。”早饭后,我像往常一样,格守着上班的时间,徒步走回机关。走到大街上,如同一个久居外乡的人回到了故乡,我所熟悉的街市,没有多少变化,只是多了几分清寂,几分萧索。那街道两旁的店铺敞开着,迎透着烟霭中的晨光,冷峭的风从滦河的谷地那边吹过来,穿过空荡的街市——冬天的早晨,没有多少行人,偶尔有两三个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走过来,有男有女,年纪都在十几,岁,大约是本县的中学生。那些女孩子特别的好看,她们一般穿着军绿色的上衣,或全身都是军绿色的,头上戴着一顶“军帽”,帽子底下压着两根黑黝黝的短辫子,肩上斜背着一个绿色的背包,美丽、天真而又飒爽的模样,真像是不爱红装爱武装,并且是投笔从戎了。最醒目的还是那街道两旁墙壁上的大标语,上面写着“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类的口号,斗大的字笔力雄浑,震人心魄,我仿佛走进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在县委机关北面的不远处,是“文革”接待站,在它的门前,有红卫兵进出,我遇见了接待站的赵振山同志,他告诉我:“这些学生是来这里领粮票的,准备到外地去串连。”我说;“那还还吗?”他说:“都记账了。”“天晓得以后怎么还。”我心里嘀咕着,走进接待站办公室。 接待站办公室是一个很宽绰的房间,墙壁上张贴着十多张大幅的彩色照片,突出的画面是毛主席和中央其它领导同志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的盛大场景,毛主席带着红卫兵袖章,向聚集在广场上的激奋的红卫兵挥手致意。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画面,正好刘进友同志也在那里观看,他招呼我说:”钟惠,你看,少奇同志站在边上了。”我靠近他去看,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央领导同志的排序中,刘少奇同志站在毛主席右侧第七、八位,就是说从左右两边计算,他已从过去最靠近毛主席的位置,后挪了十几位。我们不再说话,从进友的眼辛中中,我看到了疑惑一与不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中共中央的《决定》说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革命运动。 怎样认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我们从文件中领会,是在社会主义时期进行“反修防修”的怠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文化大革命是这一理论的实践。但是我们对中国是否有了修正主义的现实,还不大清楚,对这场运动的总趋向,也不大了解,所以在急剧发展的形势而前,在突发事件面前,又总是感到困惑与不安。刘进友同志所表示的关切,也许反映了众多党员的心境。 4.接受新使命
我从“文革”接待站出来,便径直地来到县委机关。县委机关宽敞的院落和几排房屋,依旧是老样子,只是它的冷清与沉寂,却让我平添了几分压抑,我久违了岗位,此时又心无依附,也便有些失落,可是,就在这时我接受了一项新任务。在院内,李景禄同志招呼我到组织部去,说李程国同志找我(李是县委常委农工部长,后来听说代理组织部长)。我随李景禄走进组织部,李部长正站在办公室,他见到了我,就径直地对我说:“经常委研究,让你到人委办公室任主任。”我们俩都坐下来,他继续说:“现在人委办公室没有正主任,只有一名副主任,你去是任正主任。”又说:“眼下那边急需要人,你现在就过去,先通过会议宣布任命,以后在补文字。”李景禄在一旁也补充说:“现在开不了人民委员会。”(意思是对我的任命,要待情况允许时能召开人民委员会议了,再发文字。)我问:“还带不带手续?”李部长说:“不带,文字都以后补。”(那时候为了避免红卫兵的干扰,县委已不再有公开的动作。)我意识到这是县委根据当前的形势,做出的安排,但我过一去一直做党务工作,对行政工作并不熟悉,我想我即使不接受这一任务,今后也会有适合我的工作,但是面对眼前的形势和领导的信任,我还是接受了这一任命。
1967年元旦,悄然而至。在头天晚上人委机关召开的全体干部会上,副县长林祥代表县委常委宣布了对我的任命,次日上午,我就来到了新的岗位。来得是那么匆忙,以至我走进人委机关以后,才发觉这天是个节日(厨房正在准备节日的午餐);来的是那么急促,没有人向我介绍情况,我也无从问起,县长傅景瑞还滞留市委(在我来人委头天,我们曾见了一面,以后就没见到他,大概他只回来一两天就返回市里去了),常务副县长李玉山每天要到机铁厂向造反的工人交代“问题”,副县长李永丰从“四清”前线回来还未上班,只有副县长林祥一个人留在机关。机关支部书记人事科长朱庆玉因病休假,由我接任支部书记,但是我对人事一无所知,仿佛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在人委办公室,只有一名副主任,两名科员和一名打字员,还有作内勤工作的。整个机关人心慌乱,政府的工作也几乎停滞。这时我才进一步领悟到县委派我到人委来,不仅是要我支持行政事务,主要还是让我协助领导把握人委机关的局面,但是这样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 1967年1月21日,我去唐山参加盲人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提高各级政府对残疾人生产生活的重视,并动员造反的盲人回家,可是会议刚开到第二天,市里就发生了“夺权事件”,这次会议在一位民政局长的支撑下,和市“盲人协会”的配合下,总算开下来了。会后我带着迁西的几位盲人返回了迁西。 我回来后,发现迁西的形势也有了变化,人委和其它机关部门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我到办公室刚坐下来,打字员孙敏就找来,板着脸对我说:“文革以来县委任命的干部,我们不承认,你先回县委吧。”我听了以后,感到气愤,我想说我是县委任命的,你们有什么权力赶我走,但又一想,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既然他们造了反,你留下来,他们也不会听你的。想到这里,我直视着孙敏,不再说话。就这样,我到人委办公室工作一个月,前二十天很少有行政事务,后十天只参加了一个会,就被造反的下属轰走了。 5.代理书记之死
我回到县委机关,在院内遇到到了刘进友同志,他对我说:“王怀忠同志自杀啦。”“为什么?”我吃惊地问。他告诉我:“中学的两派红卫兵都缠着他要他表态谁是革命的,他不好直接回答,就对‘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说,我压制了你们,又对‘卫东红卫兵’说,我欺骗了你们。因此受到了其他常委的批评,思想有了压力,就投滦河自杀了。”刘进友还告诉我:“没有给他一口棺材,就盖一片席子,拉回家去了。”最后他喃喃地说:“他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妈呢。”惋惜与不平溢于言表。赵振山同志也告诉我:“多少天来,红卫兵一直纠缠他,他不得体息,连看报纸的时间都没有,也许他的脑子乱了,思想承受不了啦。”我们都是老同志,过去关系不错,所以有话愿意跟我说。
王怀忠同志是个老干部,过去在南方当过地委组织部长,回迁西以后任县委副书记。在县委书记去地区搞“四清”以后,他代理书记,负责“后方“工作(重大问题还要向在“四清”前线的县委书记汇报和与其它常委沟通)。他是农民出身,为人忠厚朴实,在县委一班人中素有长者之风。我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是记录1966年国庆节庆典的,有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的盛大场景,王怀忠站在观礼台上的人群中,翘首张望如潮的广场。对于一个忠于党和人民的老战士,他很想跟着毛主席的路线走,但是红卫兵的冲击,又往往使他处于困难的境地。也许在红卫兵的逼问下,他婉言地回答,是想避免两派学生的冲突,化解两派学生的矛盾,所以宁愿把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却不想招来更多的麻烦,有的红卫兵对他更是不依不饶,在受到其他常委的批评以后,思想增加了压力,便投河自杀了。在那个年代,自杀就是叛党,他被开除了党籍。一个忠诚的战士走了,走的是那么凄惨,让一切正直的人为之伤悲。 6.祸起萧墙
红卫兵运动从校园扩展到机关、企事业,以至整个社会,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在县委机关也先后成立了“敢字号”和“劲松”等组织。我回县委机关以后,也曾有人要与我组建一个组织,我没有同意,我不愿牵头做这种事情,但是当李景禄同志要我参加“劲松”时,我同意了,因为他们都是组织部和监委会的,我想我应该和他们在一起。
后来“劲松”又与其他组织联合组成了“灭资兴无造反队”,人数就比较多了。至此除去领导干部和其他被认为“有问题的”干部以外,绝大多数人都分别加入到“灭资兴无”和“敢字号”这两个组织了。在这以后,大院的形势,越来越不稳定,在几天的时间里,相继发生了意外的事件:一是县委的核心出现了分裂。有一天,我在县委院内碰见了县委副书记孟英同志,我们走得很近,他悄悄地对我说:“刘任英有海外关系,他的岳父在台湾。”这使我感到突然,我知道他认为我这个人靠得住,才向我说的,但我马上又意识到他的用意,所以只是望望他,没有答话就走开了。 这件事一直使我不安,也一直不敢对旁人讲,李景禄同志是做干部工作的,有一次我从侧面向他透露了这一情况,他说:“刘任英的岳父在天津(也许说在北京)给一个资本家当秘书,在解放前跟资本家一起跑到台湾去了。”他为什么知道得这么清楚?我不能肯定李景禄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的这个情况,但他是在刘任英出去搞“四清”以后,才调到组织部的,刘又是省管干部(或市委代省委管理),他对他的这些情况不一定了解。孟英是个老同志,而且过去在地区做过公安工作,在县委也分管政法工作,有条件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加之他又向我说过此事,我就怀疑是不是孟英也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 刘任英是县委副书记,在县委书记张逸生同志调市委以后,任代理书记,此前他己担任地区“四清”总团的副政委(曾经在总团留守,回县比较晚)。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搞完“四清”,他就会被正式任命为县委书记。孟英此时抛出他的“海外关系”问题,就是要在政治上孤立他,进而把他搞下台。我不知道李景禄是怎么想的,但是后来“灭资兴无造反队”就贴出了大字报,揭发了刘的海外关系问题,我想,他一定也在其中起到了作用。 二是“敢字号”夺了县委办公室的权。“敢字号”主要是由县委办公室的内勤和政交人员组成的,还有团委和监委的个别人参加。有一天,听说“敢字号”夺了县委办公室的权,我不在现场,不了解情况,过后遇见了县委办公室的刘进友同志,他对我说:“他们要我交出办公室的钥匙,我没给”,他摸摸自己的口袋继续说:“钥匙就在我兜里,我能随便交给他们吗?”刘进友同志做得对,“敢字号”夺权是错误的,他们是在“上海一月风暴”和全国夺权之风的影响下,采取的盲目的过激行动。不过根据刘进友同志说的情况,他们占据了办公室,拿不到县委办公室的钥匙,也就拿不到县委办公室和县委的印信,这夺权的作为就打了折扣。“敢字号”的行动,受到了有关方面的批评和指责,后来他们退出了办公室(这大约就是后来在史料中记录的党委夺权)。 三是“灭资兴无”扣留了朱长欣。朱长欣同志原是迁西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前不久调杨店子化肥厂工作,不知他为什么来到了迁西,被“灭资兴无”的人扣下了。那天,我从组织部南排的一间屋子的门前走过,门吱的一声被拉开了半面,我看到他慌张的样子,立即走了进去,问他;“你怎么来了?”他说:“我被扣下了,你是不是跟他们说说先让我回去,以后有什么问题再找我。”我当即答应,转身走到另一间屋子。这是“灭资兴无”的活动室,很多人都在那儿,有李景禄,他是“灭资兴无”的主要头头,还有张风山,他也是组织部的,是从“四清”前线回来的。我对他们说:“让长欣同志先回去吧……”我的话还没说完,张风山就反驳说:“那怎么行,他在发展党员和任用干部上有很多问题,怎么能让他回去呢。”没有人搭碴儿,李景禄也不表态。张风山所说的问题,涉及了我,因为我就是具体做党建工作的,而且人们知道我和朱的关系,同样的话,看谁说,我的话不顶用,无奈走出去了,想找个机会跟个别人沟通。长欣同志站在那间屋子的门里望着我,像是急切地等待我的回音,我却不能走过去,因为如果被别人看见了,我说话就更不灵了。后来,当我们回到屋里再次议论此事时,李景禄终于表态,同意让他先回去了。 朱长欣身陷“灭资兴无”,有惊无险,终于离开了迁西,但是对他的问题,有的人并没有放手,后来还是我出具证据,帮他在这些问题上得到了解脱。所谓发展党员问题,是指六二、六三年在文教卫生系统发展的几名知识分子党员,他们都是经过党组织长期培养考察,经过我了解和谈话,有的还旁听了支部大会讨论的情况,而后提到部务会讨论通过的。按照规定履行了程序,即使有的支部有纸漏,也与朱长欣同志没有关系。对于干部的任用,凡是县委管理的干部都是经过组织部考核,报常委讨论通过后任命,并不存在问题。主张反对朱长欣的人,都是他经手调入组织部的,而今却成了对头冤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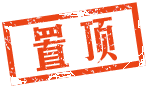
 匿名
发表于 2011-7-12 10:18
| 来自河北
匿名
发表于 2011-7-12 10:18
| 来自河北 匿名
发表于 2011-7-23 13:05
| 来自广东
匿名
发表于 2011-7-23 13:05
| 来自广东 匿名
发表于 2011-7-23 15:32
| 来自广东
匿名
发表于 2011-7-23 15:32
| 来自广东 匿名
发表于 2011-7-24 14:00
| 来自广东
匿名
发表于 2011-7-24 14:00
| 来自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