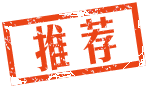以笔为犁,从平原到丘陵 (计空格5817字)
——读张凡修的诗集《丘陵书》
◎王志勇(唐山诗人、作家、书法家)王志勇博址http://blog.sina.com.cn/u/1789951943
辛卯年春节前夕,即腊月27下午,凡修兄亲自跑来市里,将腊月25刚收到的、他第一本诗集——《丘陵书》先期10本样书中的一本交到我手里,让我有说不出的感动。书作得素雅、精致,捏在手里,薄厚恰好和《吉檀迦利》或《朝花夕拾》相差不多。伴着春节的爆竹,诗集《丘陵书》成了我阅读餐桌上的一道美味佳肴。

一
《丘陵书》收录的大部分是诗人张凡修于2009年、2010年两年内的近作,定稿是在2010年4月,这是一个异地游子献给辽西的歌。
张凡修在辽西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将近4年的时间,这里“遍地丘陵,山地贫瘠,十年九旱,风沙满天”。当地人说:一年只刮两次风,每次就刮六个月。县与县之间,一般都相隔八、九十公里。人均八至十亩地,但粮食亩产量低,没有水浇地,仍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随处可见小毛驴在丘陵窄道间负重踽踽独行,大部分地区的机械化程度只相当于农业发达省份上世纪60年代水平。贫困与荒凉,让他真正了解了农村。
张凡修的诗歌写作中断了整整18年,有过写作经历的人都知道,这么漫长的撂荒期,不管诗人的写作基础如何,想重新拾笔,几乎不可能。对于张凡修而言,过渡期同样艰难,否定自己是痛苦的,唯壮士敢断腕,置之死地而后生。2006年以来,张凡修开始恢复性写作。2009年后半年,仿若神助,一飞冲天,他的诗歌创作迎来了自己的井喷期,每个月都有十几首成熟诗作新鲜出炉,在网络上受到大量热捧、热评和转载。那种高产、高质、持续喷发的快感和一泻千里的痛快淋漓,让每一位关注和喜爱他诗歌的人都能真切、真实地感受到。
二
张凡修的诗选取的大部分是生活的截面,他用诗记录着他正在感受着的生活。他写的依然是农耕文化——农事,农民,农村,构成了他诗歌作品中独到的“三农”风景线;乡土,乡魂,乡亲,赋予了他诗歌作品中鲜活的血脉。
他的诗摒弃了肤浅的抒情,将自己对土地内敛的爱化作人生体悟的深度,像一把锋锐的犁,掘地三尺,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容易让人忽略的诗意,从而还原了一段沉寂的历史。
地域环境的改变不可能不对他的创作产生影响,独在异乡,站在丘陵之上,原来身处庐山其中的故土,成了诗人向西遥望的一个焦点。故乡,他乡;平原,丘陵,在参差对照中,诗人的回忆被磨练成新的发现。就诗人的创作而言,他的文本写作,也真正实现了风格标识的塑造。
张凡修的故乡玉田鸦鸿桥,作为京东名镇,远近驰名,闻名遐迩。那里的庄稼人天生有一种经商的才能,然而处于一个长期重农抑商的历史环境中,所辐射到的京、津、唐地区乃至东北一带,鸦鸿桥人不但没有遭到恶评,甚至连微词也没有。我常纳罕:鸦鸿桥人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闲时经商,忙时务农,亦农亦商,一身二任,张凡修可谓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作为一名勤劳、能干、精明的农人,张凡修是庄稼院里的“好把式”:他熟谙24节气,什么节气干什么活,耕、耙、犁、种、栽,使熟了各种农具,并将它们巧妙地与亲情缝合起来,自然而毫不牵强地上升到美学范畴。商业是趋利的,经商的人却可以做到赢利而不势利。传统的农业,在今天已悄然完成了与现代文明的嫁接。
好地长好庄稼,好人写好作品!张凡修在丘陵地上找到了一块又暄又透的好地,种下的文字,终于有了沉甸甸的好收成。
三
农耕文化渐行渐远,传统的农耕方式已成原始、落后的代名词。土地是沉默的,土地上的劳作是沉默的,汗滴禾下土,是劳作者与土地唯一的交流方式。诗人的双脚踩入泥中,在闷热难捱、密不透风的高粱地里,他直起累弯的腰板,突然有了一种“代言”的冲动,使你不得不倾身细听——
交出铁轨。
秸秆躺下来,让远方的亲人
从自己的身体上回家
无论走多远,走不出高粱地
左旱路,右水路
秋风一年一吹
铁轨一根一根站着,长高
交出行程。
高粱地掏空秋天,掠过瞬间的苍老
穗子内心辽远,扎成一把一把笤帚
扫净了通往村外的冬雪
无数亲人,又坐在高粱地里
他们都成了
开走的火车
——《火车开进高粱地》
这是我尤为钟爱的一首诗。以“火车开进高粱地”为诗题,省略了这句歇后语的下半截——没辙了。原本是没有出路的苦闷的“诗题”,经诗人自然、紧凑的描述,过渡为意味深长的怀亲之作,嘹亮、悠远、深沉。高粱作为农作物的象征,与现代工业的象征——铁轨,巧妙地完成互文。开走的火车暗喻生于斯、劳作于斯、埋葬于斯的祖祖辈辈勤劳的先人。死亡,不再是一种给人带来幻灭感的悲哀结局,而是劳作者完成劳作使命后向另一个世界的远行。劳作者向死而生,劳作之美在于让劳作者变得“内心辽远”。
在张凡修的诗歌中,他不会单一地歌颂一样事物,土地,庄稼,亲人,甚至是死亡,总能在他的笔下紧密地融为一体,相得益彰。诗歌是觉悟自身的一种方式,那进入我们生命的,也必将进入诗歌,那留存在记忆深处的,也必将在诗歌的深处蛰伏。张凡修用他挤掉水分的诗歌“干货”告诉人们:自己的诗歌,不是一位摆脱了生存威胁的农人闲散时光的白日梦。
四
庞德说:“诗人的责任是净化该民族的言语。”现代诗歌致力于描写真实的纯粹。无疑,准确地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就是诗人的天职。
大量散落于民间的、带有浓厚地域色彩的俚语、俗语、歇后语,作为一笔价值可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间经验与智慧的凝结。我尤爱那些带有脑筋急转弯特点的歇后语,它们是民众靠口碑流传的艺术瑰宝,虽然形式短小,只是片言只语,但却凝练得犹如精金,纯净得仿佛水晶,如粒米微雕,呈大千世界。一切坚不可摧的都烟消云散了,而这些语言的活化石,却口口相传,留到现在。
诗人张凡修,细心地打捞、收集、擦拭、端详,然后谨慎而纯熟地把这些语言精粹嵌入自己的诗行。“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民间俗语的大量引入,不但增强了张凡修诗歌语言的口语化成分,更让这些村俗俚语有了荣登大雅之堂的机会,通过诗歌文本,让这些行将被新人类遗忘(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语汇得以化腐朽为神奇。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凡修不单是丰富了自己的诗歌语言,也是对民间口头文学与现代诗歌的有效融合做出了尝试性的贡献。
在阅读张凡修诗歌的过程中,你完全可以体会到诗人竭力规避抒情的企图。大量的细节入诗,白描的手法,零度情感的叙述,滤掉一切抒情色彩甚至到了刻意的地步。没有编造,没有凭空想象,笔底之言,除了躬身亲历,俱是眼睹耳闻。诗人仿佛害怕自己跌入一种传统的窠臼:只要抒情过浓的作品就空洞直白,缺乏诗歌的味道,也容易高蹈。
诗人到底对反映时代有没有义务?在当代诗歌创作中,这似乎成了一个容易引起激辩和误解的话题。这真的是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两难取舍吗?张凡修的很多诗作,浅者不觉深,深者不觉浅,这是一种很难抵达的境地。不唯如此,他更善于将一些重大题材和重大事件置于不动声色的描述中,从而让整首作品产生强大的张力和出奇的效果。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饥馑,是一场世界性的灾难,更是从那个艰难岁月里走过来的人,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这场导致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悲剧,首先是以家庭为单位上演的。世界上最大的一条玉米带横贯河北玉田,河流纵横,沃野千顷,物产丰饶,人杰地灵,历史上几乎没闹过饥荒。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诗人的故乡同样在劫难逃。《春天慢》这首题目貌似婉约的诗,通过对一只空碗的诅咒(让我想起一部名叫《狗日的粮食》小说),反映了恰恰是在青黄不接的春天,忍饥挨饿的人们对步步逼近的死亡威胁的恐惧。
而在另一首诗作《母亲的胃》中,诗人又从别样角度展现了那饥荒年月耸人听闻的一幕。在《母亲的胃》中,诗人写到:
后半生。母亲的胃一直空着
一九六一年,母亲吃得太饱
那年的母亲给公社大食堂推磨
囫囵下许多生粮
不嚼。只暂时存在胃里
回家后用筷子捅进喉咙
一口,一口,再吐出来
未消化的粮食喂饱了奶奶,爷爷
也喂饱了爸爸和我
……熬过三年。后来习惯成自然
只要看一眼装过米饭的空碗
她就会将吃进去的东西吐出来
前年,母亲离我而去
没带走一粒粮食
这首诗写的不动声色,惜墨如金,句句惊心,环环紧扣。起手悬疑,高潮惊悚,结尾于无声处听惊雷。全诗无一个生僻字,无一个修饰词,却达到了回音不绝,过目难忘的阅读效果。这是应该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的一首诗,不是为了“忆苦思甜”,而是要让世世代代记住这个国家对一位母亲的亏欠。母亲的胃,装下了整个民族的苦难。
孔子的“九五”塑像悄然立于长安街上的天安门广场,2500年的历史长河,肯定了儒教作为准国教对民族绵延生存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百善孝为先,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诗中的母亲仍恪守着中华民族伦理纲常的底线:婆婆,公公,丈夫,儿子。唯独自己排不上位次,要排,也肯定是最末一位。非常时期的“最末一位”,无疑等于最先牺牲掉的第一位。母亲伟大、彻底的牺牲,让“偷”(况且粮食本来就是属于他们的)的行为变成催人泪下的义举。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做出巨大牺牲的又岂止是母亲?而是整个农民阶层。梁漱溟关于“九天九地”(即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的言论,最终引发了与领袖的一场被写入“五卷”的激烈争辩。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以及终身不变、铁板一块的户籍制度,不但在物质收益上大大地损害了农民老大哥,还在社会身份上给农民的心理投下了巨大的自卑阴影:
我一直够不着高粱的高
从未见过高粱花的样子
只是那年代父亲的头顶上
敏感的触须,飞起,落下,飘散
似乎有深层的阴影
我怕,提及
——《高粱花》
高粱花是美丽的,是人为的“分别心”让这种作为农作物的美丽植物蒙羞。但“这时候的父亲,腰杆总是挺得笔直”。肉食者鄙,下下人有上上智,古来如此。父亲的不言之教,让“我”受益终身。一首反映了几代人、累计数十亿农民,因长期歧视性身份而带来“隐痛”的诗,就这样以高粱花“变换着粉红、微紫,淡白的表情”,为无声的历史做出了呐喊的注脚。
五
要读懂张凡修的诗歌作品,且不说没有紧随时代的诗歌阅读经验不行,欠缺农村生活和农事经验更不行,甚至还要具备对机智与农民式狡猾的会意。加之,诗人删繁就简的创作胆识,常常因诗行的跨度、短路、断裂而造成理解的盲区,思维如同攀悬崖、穿峡谷、越海峡。大段大段的留白,起伏跌宕的结构,一波三折的演绎,出人意表的结局,常常让诗人的作品增添了诗歌以外的喜剧效果。比如《中年之诱》、《落枣时节》。
张凡修坦言自己并没有看过杂七杂八的书,他诗歌的泉眼大多以生活经验的触动为主,是从生活中撷取诗意,而非从诗歌中孵化出诗歌,我以为前者更见功力,这也使得他的诗歌更具原创性。他曾为本地的诗歌作者写过《井位·湿泥·泉眼》的创作谈,形象生动,真实可信。由此可见,诗人对诗歌题材和角度的选取向来不是盲目的,而是理性和有章可循的。
多少在生活中打井勘探的诗人,最后自己也掉进了自掘的陷阱,张凡修避免了这个悲剧,是因为他可以从经验出发,但他从来不为经验所囿。私下里,诗人曾表露过对汤养宗、胡弦等诗人诗歌技艺的倾慕。诗人是自由的化身,不管脚上系着什么样的锁链,当自由的灵魂舞动起来,从感性的声音里写出音乐感,所有的锁链都成为迷人旋律伴奏的音节。
与诗人闲聊时,他曾告诉过我,自己从来没有写过爱情诗,对政治也不感兴趣。写爱情诗的人太多了,张凡修没写过也罢。中国的老百姓最有理由对政治不感兴趣,在民间,政治和摊官司一样,是一种晦气和不祥之物。避谈政治,是每一个顺民自保的底线。就生存层面来说,没有大人物与小人物之分。一名宰相一生中下跪的次数要远远多于一位终日在田野里耕地的农夫。
张凡修钟爱属于自己的小日子,这不是仅求温饱的小农意识,而是体现了农民最淳朴的对土地的情感,以及实实在在把握幸福的智慧(《我有小日子》);诗人用独具的眼光,发现着芸芸众生中不起眼的、普通人身上的价值(《在于》);他用悲悯之心关注着底层民众的生之艰难(《黑水五金店》、《老舅的腿》、《一沓钱的泪》)……
张凡修来自乡间草野,历练于京东名镇的商海,他沟壑纵横的面颊,他时时紧蹙的浓眉,他中气十足的大嗓门,非但让人从他身上找不出一点促狭与卑微的影子,甚至多多少少还有一种不怒自威的凛然之气。他随和,诙谐,爱结识80后、90后,在这些后生们面前,他既不托老自大,也不临流叹逝,“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他爱挑人诗歌上的毛病,口直心快,甚至不辞劳苦地为他人改诗、评诗、荐诗。他这些鲜明的性格特征,并没有得罪一些人。因为所有的人都心明眼亮:只有小人才不知悔过地逞口舌之利,而张凡修不是。他纯乎为了诗歌,为了让同行写出更多的好诗。他的诗歌创作理论,浅白如话,大俗大雅,却是真招实货,可以推广的独门绝技,成为很多中、青年创作实践的指南。
诗歌是不分阶级和阶层的,甚至也不分性别。因为并没有“工业诗人”、“投资诗人”与“农民诗人”相对应或相并列。当张凡修写诗时,他已不再是农民,而是一个诗艺娴熟的诗人。诗歌不是让他免于劳作的一种借口,现实中既无可能,主观上也不愿意。“诗歌是对世界正常转动的琐细(碎)的反映”(史蒂文斯)。我们关注的永远是为诗歌贡献了什么,至于诗人隶属于哪个领域和阶层,对诗歌而言,实在无关宏旨。给诗人贴上“森林诗人”或“石油诗人”的标签,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习惯手法——文学必须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服务。如果我们轻忽了“首届全国十大农民诗人”荣誉桂冠给张凡修的激励作用,未免有些不食人间烟火,但如果我们仅仅把张凡修定位于一名“农民诗人”(哪怕是“十大”之一),也同样是对张凡修诗歌作品的低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