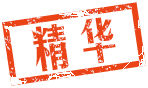|
开往远方的灵魂动车 ——凤凰诗群阅读印象 辛泊平
陈超先生说过,秋天是他读诗的季节。西风,黄叶,容易撩拨心扉的事物,是背景,也可能就是心境,彼此伤害,亦可能相互擦亮。一种久违的人生状态,有心灵的律动与参与,有灵魂的叩问与追随。阅读,即是慢下了脚步。期待月夜下一声孤单的虫鸣,亦或是阳台上的一地月光,那些错落的文字,是新朋的呼吸,是故友的掌纹,熟悉或者陌生,都让人怦然心动。
从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的视觉震撼中走出来,无数次默念一个并不陌生的名字——唐山。是的,这个名字中包含着诸多的意义、诸多的情感。那里有过辉煌的文明,有过惊心动魄的灾难,也有过传奇般的凤凰涅槃。现在的唐山是新的,新的面貌和新的脚步,然而,总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在发生。正如唐山,唐人街不是它的名片,地震当然更不是,想到唐山,我们想到的是近代的工业和煤炭,今日的富豪以及在最近中闪现的群体感恩。在这些光坏下面,从硬指标里走出来,我看到了唐山的另一张文化名片——凤凰诗群,然后慢慢欣赏,从心灵出发,抵达另一个心灵,并于此中,慢慢咀嚼别样的生命秘密和心灵节拍。
亚里士多德说过“准确的判断力是好作品的基础和源头”(《论诗学》)在我看开,东篱的写作经过从《唐山风物》到《晚居》的反思、经过从向外部探究到向内部挖掘的完美转身,越来越体现其诗歌写作的坐标意义。在凤凰诗群中,东篱无疑是一面旗帜,是众望所归的“带头大哥”。在他庞德式的对同代后辈诗人的提携(刘波语)的同时,他的写作却越来越谨慎,也越来越简约和清晰。东篱主张诗歌“有话好好说”,这一点我虽然不太赞同,但完全理解他之所以这样坚持的良苦用心。作为凤凰诗群的领袖和当代著名诗人,他的写作带有示范意味。所以,他的一招一式都必须力求准确、到位和完美。这样的写作当然缺少了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自由和率性,但却获得了一种写作精致化的内驱力。他不得不一次次自我追问,自我反诘,自我审判,自我推翻,自我磋商,最后达成情感与技术的高度集约,以完成诗人对自我的要求与期许。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也是一个自信的选择。在这个类似凤凰浴火的自我锤炼中,东篱为诗歌写作赢得了现实的尊严,那就是,诗歌不可以是那种口水泛滥,不可以是那种投机的段子写作,更不能是那种贩卖肉体、把诗歌当作行为艺术的即兴表演,它需要物质也需要心灵,需要情怀也需要技巧,它是“生命与语言的双重洞开”(陈超语),是语言艺术最敏感的神经、最优雅的肌肤。从某种意义上说,东篱当下的选择,既是诗人对诗艺的高度确认,也是诗人向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当代诗坛亮明了自己的立场,那就是:对清浅的小情小调说“不”,向无限崇低的诗歌(情怀的、技巧的、灵魂的)宣战。
在我的印象中,张非颇有些《天龙八部》里萧峰的影子,尽管外部形象有很大的差距,但那种胸怀和气度却有相通之处。在凤凰诗群里,张非既是后勤部长,又是诗歌写作另一极的旗手。和东篱的内敛、优雅不同,张非选择的是“降龙十八掌”般力度的表达。无论是描摹北方草原的风物,还是书写当下的都市情怀,他选择的都是长枪骏马,呼呼有声。他的眼界是开阔的,所以,他才会轻轻弹去沾在睫毛上的浮尘;他的胸怀是坦荡的,所以,他才会淡然一笑,直面污浊不堪的人情世故、尔虞我诈,心甘情愿地充当被被人喝光的酒瓶和用过的筷子。以德报怨,这是修养;赠人玫瑰不求留香,此乃境界。或许,正是由于张非有如此的胸襟和宽厚,他的诗歌才那样俊健和硬朗,那样坦荡和敞亮。即使是《酒后词》那样旁若无人的内心独白,也充满了男人的深情与豁达,男人的柔软与宽容。可以这样说,张非的诗歌不圆润(有些语言还显突兀),那是因为他不忍磨去自己的棱角,有缺憾(比如节奏上还有些粘稠,舒展的还不够),那是因为,他要捍卫缺憾的力量。然而,恰恰是因为诗人这种自信的醉后击筑,才成就了他独特的金石之声、骨骼之美。作为成功的商人,张非身上没有那种铜臭,作为诗人,他血管里流淌的,却是那种热情、坦荡、峥嵘的血液。这本身就是诗歌的一部分,能如是,已经足够,夫复何求?
唐小米是凤凰诗群中的才女,她的诗歌有充分打开的性别意识。但她的性别自觉不是诗学的策略,更不是为了吸引眼球的身体表演,它只是诗人打量世界、感受世界、回应世界的、自然而然的身份选择。在这个依然是男权主义主导话语权、女权主义暧昧不明的时代,女性特征十足的诗歌,要么招来卫道士的非议,要么得到别有用心者的追捧,反正就是得不到公正的评价。而唐小米的诗歌,就那样丰盈、纯净地站在那里,让“君子”敛容,让“小人”无声。因为,唐小米的女性诗歌,既有真实的女性欲望与困惑,更有母性的奉献与宽厚,它不求仰视和膜拜,但也绝不容许轻薄和亵渎。从她的诗里,我读到了细腻之下的决绝,温柔之中的刚烈,读出了对生育的迷茫和母性给予的无私与慷慨。可以这样说,这种融合了多种气息的女性自觉与内省,使得唐小米的作品既有人间烟火的残缺与温暖,又有柏拉图式爱情的虚无与自足。因为,它既是诗人肉体的切肤感受,也是灵魂的健康呼吸。唐小米的语言是扎实的,犹如昔日那些巧手妇女纳的鞋底,针脚密实、紧凑,细致均匀,既有贴心贴肺的温度,也有超越实用的美感。面对这样的诗歌,你无法轻佻,只能随着诗人一起,梳理那只有女性才会有的爱与恨,伤与痛,悲与欢;然后,以全新的角度去打量那些宁静的女性,乖张的女性,压抑的女性,隐忍的女性;然后,一点一点感触,一点一点融化,一点一点理解,然后,自觉践行生命之间的彼此坦诚与互相尊重。这就是诗歌的道德力量,它忠实于生命,拒绝调侃的漫画和轻率的虚构。
不知道为什么,阅读凤凰诗群中的另一个才女黄志萍,我会不时想起小说家迟子建,想起她的《沉睡的大固其固》,想起她的《向着白夜旅行》,想起那种没有边界的心灵故乡,和没有始终的极地之旅。然而,在那种天地一色、地平线消失的地方,留给读者的并不是那种让人心慌的空旷和四顾苍茫的恍然,恰恰相反,在那种没有边界的心灵故乡,在那个忽略月台的极地之旅,诗人始终如灵巧的小鹿,睁着她那好奇的眼睛,丈量着心灵与尘世的距离。这是一种放飞灵魂的穿越。越过滚滚红尘与词语之林,有过小小的惊慌和幸福的惆怅,诗人最终并没有停在哪个地方,而是继续上路,“带着一颗必然的心寻找”(《银城铺》),是寻找一个流浪的人,寻找散落的菜籽和遗失的密码箱,还是就是寻找寻找本身,这些都不重要,诗人似乎已经打定了主意,就这样在不及物的寻找中体验那种心灵的自由与灵魂的上路。相对于唐小米细密的语言,黄志萍的语言是轻盈的,但不是干燥的那种,而是淌着露珠的那种轻盈,如雨后的草叶,湿润而鲜亮。这既是诗人对语言的高度敏感,更是生命在纸张上的天然流淌;它犹如山上的清泉,叮叮咚咚,不假人工,但自成天籁。正因如此,黄志萍才能通过那些短短的句子,随处搭建一座座充满童话气息的城堡,于当下弥漫的喧嚣中,挽留下一片忧伤的月光,一段任性的独舞,以及一场带着少女气息的、慵懒而多汁的梦。
在凤凰诗群中,郑茂明也是早慧的诗人。作为80后诗人,他身上没有一般意义上的乖戾和张扬,也没有那种对当下不适应的抱怨,他是平和的,宁静的。都市中的生存挣扎没有消磨掉他对事物的敏感,更没有俘获他高贵的审美。他的灵魂拒绝都市的加速度,而是无限靠近自然的季节,所以,他才会有那么多植物情结。在他的笔下,那些挤在一起的树木是有灵魂的,它们就是他前世今生的兄弟姐妹,即使是掉光了叶子,“纯粹得只剩下骨头”,也会“紧紧攫住大地”(《那么多的树,挤在一起》)这几乎就是他这一代人的生存写照。走出偏见,我们会发现,他们并非我们想当然的自私、轻浮、消极、脆弱,而是有一种抱团取暖的心灵渴望,有一种期待洗礼的灵魂诉求。这是一种强烈的内心生活,它不关功利,远离尘嚣。阅读郑茂明,我有一种复杂的感受,我欣喜于他写作的老道和沉稳:不论是谋篇布局,还是对叙述节奏、情绪节制的把握,郑茂明都是出色的;在他的诗中,你似乎看不到属于青春的青涩、躁动与喘息,更多的是洞悉一切的淡定与释然;这当然是一种健康的人生姿态。然而,对于一个年轻人,这种于荒芜中望见葱茏的心态便有了一种早来的中年况味。包括哪些打磨得光滑细致的诗句,也让人不时怀疑诗人的真实年龄。说实话,相对于郑茂明这种超越年龄的成熟,我更愿意看到一个还保留着愤青心态的郑茂明。那种激愤与不平,那种骨子里的较真,那种挑战世界的精神,哪怕是椎心的痛苦和泣血的绝望,也自有一种鲜明的棱角和声音。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看法。郑茂明毕竟以他的方式写出了属于他的灵魂律动和精神现场,而且,他已经成功地为青春的伤感打包并邮寄给远方,留下的是生命细腻的肌肤,柔软的善良,以及扎实、自足的现实之路与灵魂之旅。
刘普的诗歌是属于乡土的,这样说并非仅仅因为他的诗里有大量的乡村风物,更重要的是他那种亲近泥土、关注稼穑的情怀,以及如土地一样朴素的表达。在他的笔下,即使是一块荒芜的土地,也是和父亲血脉相连的记忆。在这块记忆的土壤里,有沉甸甸的五谷,也有割舍不掉的血缘。所以,面对它的荒芜,诗人虽然“无话可说”,但却听到了来自泥土深处的“狂躁的心跳”(《一块地荒了》)没有乡村生活经历的人永远也不会理解这种无声的疼痛,因为,那种深沉的土地情结和由此而衍生的乡村伦理,它们曾经那样结实和温暖,它无法承受由于血液缺失、劳作不再的荒凉。刘普写拔草人,写砖茶,写乐亭大鼓,这些在后现代语境中成为背景或者即将成为记忆的事物,却是让诗人沉醉的心灵醇酒。可以这样说,刘普在吟咏这些笨拙甚至粗糙的事物时,他的呼吸是舒缓的,心跳是均匀的,因为,它们不仅仅是过时的乡间风物,更是都市中怀旧的影院,在那种恬静、质朴的镜头中,诗人看到的是生生不息的大地生长,是绵绵不绝的生命留恋。刘普的语言也是朴素的,和那种朴素的情感一致,口语,明快,而又充满了庄家成熟的味道。诗人清楚,在现实中他已经无法回到生养自己的故土,但他的灵魂却一直在期待,那种充满惆怅也充满诗意的“落叶归根”。
带着镣铐跳舞,并跳得隐忍,跳得热烈,跳得有古典的韵味,有当代的情怀,读王志勇,我读出了这种感受。作为唐山大地震的受难者,王志勇身上打烙着强烈的唐山印记,然而,他没有把这种苦难当作卖点来兜售,更没有陷入生命的灰色地带诅咒阳光。相反,他和阳光是天生的兄弟。在他的诗歌里,没有对命运的诋毁,没有对世界的仇恨,更多的是和他所处的时代促膝谈心,以及对人间烟火的坦然接受与深刻的感恩。他劝诫女儿要有耐心,他渴望和妻子在今世和来生都能结缘,即使是回顾昔日梦魇一样的地震,观照今天的突来的灾难,他也没有那种压抑的悲伤,而是刚健的希望,因为他“相信太阳”,因为他的灵魂一直在“瞭望春天”。王志勇是一位有学养的诗人,他的散文厚重大气,他的评论深刻独到,这种综合写作的底蕴得益于他的沉潜,也得益于他的宁静的心态。在酒绿灯红的都市中,他不浮躁,不观望,而是埋首书桌,在另一个有别于尘世的时空里整理他灵魂的屋子。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王志勇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是肯定他身上优雅的书卷气。在他的诗歌中,还有一种批判的锋芒。面对现实的不公,王志勇没有回避,而是直面时代与生命的残缺,站在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对这个时代表达他的不满与批判。对王志勇,我个人是钦佩的。因为,他的身上有知识分子的宽厚,有知识分子的怀疑,更有知识分子的理性和峥嵘。 阅读同样是80后的唐棣,我时常惊诧于这个写小说拍短片的诗人何以有那么多的属于古典的寥落。和小说写作不同,虚构性在诗歌中是危险的事情,然而,唐棣的诗歌却有那么多真实的虚构;和短片不同,诗歌不拒绝镜头的剪辑,但过多的镜头自然会伤害诗歌的完整。然而,我这两方面的担心在唐棣的诗歌中都被他巧妙地化解了。他的宝典就是诗人自觉的愧疚,这种愧疚既是伦理,也是物质,它是诗人心中无法化解的情结,是人子抵达的献身情怀。它来自诗人对当下的双重观照,一方面,写作给他提供了一个可以躲避世俗尴尬的空间,另一面,诗人清醒的情感和理性,又不允许他忘记另一种更为实在的角色认同。在这场羞愧与高贵的交锋中,唐棣既是战士,又是统帅,同时还是胜负的最终裁决者。所以,他才会怀疑时间,怀疑生命的重量,然后“以诗为乐、孤独且骄傲”地直面现实的不堪和灵魂的尴尬。
2008年,在一个游人如织的南湖岸边,一个自称农民的老头儿在朗诵,嗓门响亮,旁若无人,那种如醉如痴的投入状态,让我一下子记住了这个稀罕的老头儿。当时心想,这个老头儿不简单,在一些诗人形迹可疑、一些诗人羞于承认自己诗人身份的当下,对诗歌如此痴迷、如此虔诚、如此大方的人已不多见。他的身上有一股你不能轻视更不能忽视的劲儿,冲着这股子劲儿,他肯定行。后来证明,我没有看走眼,这个老头儿一路挺进网络诗歌论坛,挺进民刊,挺进国刊,挺进“首届中国十大农民诗人”的行列,冲出了那个叫鸦鸿桥(玉田县)的京东名镇,冲出了那个叫唐山的城市,冲出了河北,走向了全国。这个稀罕的老头儿便是张凡修。读张凡修,我读出了那已成为诗人骨血的泥土味儿、庄稼味儿,甚至是肥料味儿。他的诗是饱满的,因为,他的诗行里是雪白一片的棉花地,是堆满谷物的打麦场,是平原大地,是家乡的河流,它们有根,根扎在土里,正如诗人自己。当然,吟咏故乡风物,这在诗坛并不新鲜,已经有那么多人在咏唱。张凡修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沉溺于乡村的苦难而不能自拔,更没有像度假的观光团一样俯视那些属于风景的村庄,而是始终与他描述的人事一样谦卑与自信,在它的痛苦中痛苦,在它的欢欣中欢欣。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张凡修的写作并没有像他的年龄一样儿知天命,一样看破红尘,一样随缘聚散。他是不满足的,在诗歌里,张凡修像一头“把待扬鞭自奋蹄”的公牛,瞪着喷火的大眼睛,挑剔地看自己在语词世界里播下的秧苗,不保守,不盲从,而是始终保持着一股拼命三郎的闯劲儿,口语就口语,书面就书面,只要它们符合自己的逻辑,有自己的秩序,那就值得尝试,值得实验。可以这样说,在张凡修身上,我看到了许多青年人身上所缺失的血管饱满的“先锋性”。
随着阅读的持续展开,我还领略了凤凰诗群闪亮星群的风采,比如路长的历史情怀与批判现实的勇气,陈小梅泰戈尔式的清新表达,青苹果的激情与粗犷,紫练、江峰、落叶等人对生命、时间的细腻感悟与婉转的呼吸,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竟,她是一个孕育已久、发展迅猛、后劲十足的诗群,是新唐山的一张文化名片。在诗歌的旗帜下,有一群人以生命的名义,跨越世故和偏见,在当下书写灵魂对当下的感受与回应,这是诗歌的承担,也是诗歌的荣耀。然而,这也是一条没有回程的旅途,一旦踏上这列动车,你就不得不一直向前,一直开往远方,正如生生不息的生命,正如没有边界的灵魂。
2010-10-13夜完稿14日定稿
来源:故乡鸦鸿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