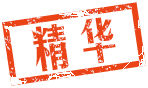|
饭后,慵懒, 从窗外透进来的光,有些刺眼。窗帘挡不住阳光,浅金黄里——太阳的一条条亮线与众不同,炫眼而灼目。推开窗,有一丝寒凉把我蛰了一下,我知道,天还是冬天的天,虽然,今天没有风。
喜欢埋在老家暖和的被窝里,把头对着窗子,等午后的阳斜斜罩住我的眼睛。即便是冬天,薄薄的窗帘阻不住阳光,文弱的阳光让心中的冷峭,一点点变小融化成蒸气,烘得心里暖。关不严的窗缝间跳进冬天俏皮的凉,拧一下我的鼻子,我眯起眼睛搜罗一遍老屋,却找不到它的影子。厢房檐下的一溜干白菜碧绿的,衬得表皮干枯的葱越发白。煤仓上,去年还有的冻豆腐,今年已经不在了,还记得豆腐上蜂窝样一个个孔,像食堂里卖的发糕。
偶尔,几只不知名的小鸟站在厢房矮顶上,房顶错落着母亲拾来的树枝,剥落的树皮被它们踩几下,婆娑散落到屋顶上,零星的尘土飞不了多高。
走出老家的大门,屋外的阳光,软软的一下铺了我一身。看看天,不太晴朗,半乳色半浅蓝,阳光没有直射下来,似在半空顿了一下再缓缓飘下来,打在身上温弱、温暖。空中投射下来的光线像父亲和我交谈时手里的那颗烟,烟气升到半空,被斜绕进来的过堂风一袭,忽散了,而父亲手里的烟还在燃着,一丝丝,青色袭不断。
停在老家的世界,让冬阳染着我,感觉这里时间没有匆匆地逝过,想留的都在你的视线里。隔壁墙上,盆子里一株干枯的辣椒秧,在冬天的风中不肯掉落最后一枚火红,老家门外对面房子墙底,那一片夏天遗留的青苔,也想留恋冬天午后阳光,颜色暗绿、夹黑。
不知道为什么,一到老家,觉得时间缓慢了,你看到的一切,除了静止再就是缓慢。向着山坡的方向,前些日子下的雪还在山路上顽固地坚持,形成一块柔润的不等边,粘在路上被午后的阳映。原来,这里还是有冬天,只不过比烦躁的城市慢了半拍。和老家一墙相隔,是三四十年前的烈士墓,小时候躺在水泥墓上,阳光晒在身上,忘记墓里的人和墓边的碑文,只知道阳光好舒服、好温暖。
胡同口的两棵香椿树挤在一起,树顶挂着两个跳笼,里面几只色彩斑斓的鸟叽叽喳喳。
老家窗台摆着几盆绿色的青株,栽在紫色、红褐色和奶白色花盆里,冬日午后的阳光倾洒在叶片上,从窗缝吹进的风,让这些植株微微地动。其中有一株是去年新插茉莉,清瘦地靠在窗台边上,叶子浅绿。
曾瞥见我家楼道通风窗台上一株被人遗弃的茉莉花,叶子都落了,花盆里的土干成一块,只有一棵奇怪形状的本兀立。冬阳透过窗玻璃照在茉莉树上,我想给它添一瓢水,又担心太阳下山后,水还没有来得及渗进土壤就结成冰,让这株茉莉花再次受伤,于是,不再动这个念头。
老家那株茉莉花栽在最大的灰陶花盆里,树冠硕大。我没结婚时,每年冬天父亲让我帮着他把花盆搬进堂屋,由于天冷,叶子掉光只剩光光的枝。父亲把鸡蛋皮倒扣在花盆里,当成茉莉花的肥料,等到了来年春天,这株茉莉花蓬勃的生出绿叶,夏天开出雪白,喷香的花。后来,家里安了暖气,那年冬天,茉莉花开了一冬,往后几年,都是如此。今年三十回家,看到堂屋还是那个灰陶花盆,里面还是茉莉花树冠小了将近一半。问父亲:“这棵老茉莉怎么变小了呢?”父亲淡淡地说:“哪还是那颗,那颗已经枯死了。”“枯死了?”没等我再问,父亲接着说:“屋子里暖,本来应该冬休的茉莉不再落叶,也没有光照,时间长了耗掉精气,就枯了。”我低头看一眼角落里的茉莉,树冠上有几颗白白的花苞,过几天,又要绽开。茉莉花几片黄绿叶子掉在地上,父亲猫下腰捡起来,慢慢走到垃圾袋前,把落叶放了进去。
今天,回家过节,我看了看摆在堂屋的茉莉花,那几颗花骨朵开成一朵朵,靠近前闻了一闻,淡淡的。而——那株窗台上的,还会发芽吗… …
2012 1 26 正月初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