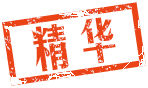从维熙,著名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家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等职。他所创作的中长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风泪眼》、《雪落黄河寂无声》、《北国草》、《断桥》、《鼻子备忘录》、《走向混沌》(三部曲)等,以现实主义手法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其中多部获全国大奖,并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韩文、塞尔维亚文等在国外出版。
从维熙出生于玉田县戴官屯村(今写作代官屯,属郭家屯乡),四、五岁时随全家人搬到玉田东关居住,十四岁时到北京亲戚家上学。1992年,年近花甲的从维熙以自己童年生活为背景,创作出版了纪实体长篇小说《祼雪》。这是一部风格清新纯净的长篇小说,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将镜头对准自己儿时生活的玉田大地,以近乎白描的手法,表现了“我”眼中的乡土和乡土里的“我”。1987年写出小说第一章后,立刻被美国西华盛顿出版的《人类学》杂志翻译发表,后又被《华侨日报》转载。
本文选录的是《祼雪》这部作品对玉田城关风土人情的描述,从中可以感受到作家眷恋故土的赤子之情。
1、一次,从维熙跟随他的小姑(俗称“老姑”)到城内闲逛,观赏了文庙等多处古迹,还曾登上城中心的文昌阁(俗称“鼓楼”),听小姑讲述曾经广为流行的一种习俗。
姑戴着它(指北平师范学校的校徽--编者)拉着我,大摇大摆地进出县城门脸儿,去瞻仰盛唐时期留下的孔庙。孔庙里有一座翘檐拱脊黄琉璃瓦盖就的“大成殿”,中间端坐着孔圣的泥塑,两旁摆设他七十二大弟子的木牌牌。小姑拉着我向孔子三鞠躬之后,便对我讲起两千多年前孔、孟桩桩轶事,听得我有滋有味,恋栈忘返。姑还扯着我的衣襟,登上县城中心的钟鼓楼,对那口唐代大钟我不感兴趣,却对大钟旁的那匹汉白玉琢成的石马,难舍难离。那马抖鬃奋蹄,状似要拔地而起,直飞九天云霄。
姑考问我说:“和尚(‘我’的第二个乳名),你猜猜这白马头为啥变黑了?”
“人摸的。”
“蒙对了。”姑说,“可是人为啥要摸它呢?”
我蒙住了,回答不出。
“传说这是唐僧去西天取经的神马。县城里凡是要出远门的人,都来这里摸一下马头。”姑说,“你四叔和姑姑们去北平上学之前,都到这来摸过马头。这黑乎乎的一片手印中,还有我的手纹哩!这神马能保佑远行人一路平安!”(《裸雪》单行本,362-363页)
五里桥在玉田城东南五里处,位于玉田去住鸦鸿桥的公路上,这里是暖泉河注入荣辉河之处。据旧县志记载,此桥最初为明代天顺年间的玉田知县乔瑾所修。清乾隆十一年,龙池庵(建于周庄村西)和尚际育以募捐方式重修此桥。在从维熙先生笔下,五里桥一带美不胜收:
“五里桥是暖泉河东流的一个河汊,离城关整整五里,河水流到那儿开始变得凉而湍急。夏日,河湾里飘荡着一条条打鱼的小船,城关集市上卖的鲤鱼草鱼鲢鱼以及王八啥的,都是从五里桥河湾打捞上来的。我还没有背起书包上学的时候,爷爷曾带我去过那儿,爷爷的雅兴既在那一条条抡网的船上,更在那桥上的三座石碑上。据爷爷说,桥上那三座石碑是明末清初的石匠打成,上边刻有玉田县令--后来当了卖酒的酒仙徐九斤(经)醉酒后写出的诗文。爷爷每次去五里桥,都对我把那诗文吟诵一遍,我装出一副听爷爷吟读的神气,两眼却有趣地盯视着三块碑下压着的三只石龟。它们好像被背上的石碑压得难以喘过气来似的。三个石龟都伸长了脖子,像是挣扎着要从碑下爬出来的模样。(同上,277-278页)
2、春节期间,玉田城乡广泛流传着贴对联、请门神的传统习俗,而且这些民俗都有许多鲜为人知的“讲究”,从维熙先生把这些民俗以及其中的种种“讲究”描绘得娓娓动听。
城关除了疙瘩爷爷的皮匠铺,还有铁匠铺,酒作坊,豆腐坊,染坊,糖坊和专糊阴间金童玉纸车纸马的殡仪铺……每到年关将至,这些作坊和铺店掌柜,便手里提着唐山麻糖和天津麻花,以及通州大顺斋的糖火烧一类的点心包儿,去求我的秀才爷爷写对联。爷爷满应满许,除去给这些掌柜书写各式各样的对联之外,还为这些不同的作坊门脸,选择和作坊行业对口的门神送去。各司其职的门神,多出自杨柳青的年画和剪纸。爷爷说,这是答谢掌柜的送礼之情。送门神贴对联的日子,每年都在过小年的腊月二十三。
“二十三,糖瓜粘。”这天糖坊的生意火红,家家祭灶时要用“糖瓜”。人们把灶王爷贴在锅灶上方,并给灶王爷献上一盘子“糖瓜”,一说是以此粘住灶王爷的嘴,另一说是让灶王爷吃了“糖瓜”,去“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沾爷爷的光,我们五个小小人儿,干上了跟随爷爷给作坊送门神、送对联的甜差。每到一家作坊门脸,掌柜的都往我们兜里装上一把“糖瓜”和花生栗子……我们得意得如同水里的鱼儿,游进了一条彩河。酒作坊门口,挂起红布条条的新酒幌;豆腐作坊门脸,悬起一面面金黄的黄豆旗儿;我家房东——皮铺的疙瘩爷爷门楣上,斜插一把为过年特制的大号红缨穗的鞭子;铁匠铺的泥巴棚外,伸出一把贼亮贼亮的铡刀片儿。只有糖作坊门脸最稀罕,一捆草把儿上面插着糖做的鸡、羊、狗、兔……人的12生肖。12生肖外,多吹了一个逗哏的猪八戒背媳妇,因而在糖坊门口,围的尽是男娃和女娃。
爷爷走到哪个作坊,那儿尽然响起迎接门神的“噼叭”的鞭炮声。我们的口兜装满了吃食不说,每个人手里还拿着一个糖坊掌柜给的猪八戒背媳妇。我非常羡慕爷爷肚子里揣着的知识篓儿,他每到一家作坊门脸和掌柜的一块贴门神时,必定要说出这位门神爷的来历和掌故。比如铁匠铺和糖作坊门脸,都贴的是一个飘着冉冉长须的仙翁。爷爷说:“这是老君爷,专司人间炉火。老君爷在天上有个炼丹炉,一年365天,旺火天天不断。孙猴儿曾被老君爷逮去,在炼丹炉里炼了七七四十九天,结果炼成了一双火眼金睛。掌柜的祝老君爷爷保佑你们作坊,一年炉火鼎盛,买卖发达。”
到了酒作坊,爷爷把粉面朱唇、耳大鼻直的女酒神像贴上门脸。接着,那一串词儿像滔滔流水,不但把掌柜说得像鸡啄米一样不断点头,连连拱手抱拳,对爷爷表示谢意;就连我们五个小当差,也个个听得目瞪口呆。爷爷说:“两千多年前有两个受百姓爱戴的帝王,就是尧和舜。尧让位给舜后,禹王治水,为除黎民百姓之灾,曾三过家门而不入。他生有个女儿叫仪狄,为尽儿女对其父的孝道,每日必为其父做饭,盼其治水归来。但禹王久久不归,仪狄随将梁谷蒸成的饭糕倒入木桶,以志对治水未归父王的思念。待禹王归来时,桶内忽溢出醇香气味,仪狄打开桶观之,见梁谷之食已酿成稀胶之状,尝了一口,香气爽人肺腑,其酿入腹,顿觉腹内温馨如火。仪狄再饮,便觉飘飘欲仙。仪狄将其酿献给父王,禹王饮之,喜称之佳酿为酒。于是仪狄成了造酒女神。现将禹王孝女仪狄肖像贴在门板,愿造酒的女神下凡,以其神方指点你们在烧锅中的佳酿,浩若三江,香飘天下!"(同上,79-81页)
3、从维熙的姥家在虹桥镇小里庄(原写作小李庄),他曾跟随母亲在小里庄常住,还曾到虹桥镇赶集,所以,他对虹桥一带的风土人情也很熟悉。
五、六岁时,我随姥姥、姥爷赶过虹桥大集,曾到过虹桥。这个镇有300多户人家,比玉田城关还热闹。这儿每逢二、五、八是小集,三、六、九是大集。乡间的七十二行,行行都在这里进行买卖交易,有的出于谋生,有的为了赚钱;房东疙瘩爷爷父子,也是这个集市上的常客。
密麻麻的人群,如求生的蝼蚁来往穿棱。在集市上,我的一双童眸,曾看见过三种打扮怪异的人:头一种身穿灰袍、剃成光葫芦头的女人,姥姥告诉我:他们是“尼姑”。第二种是戴着方巾帽,手持白色“缨甩”,迈着八字慢悠悠走路的人,姥姥说,他们是“老道”。第三种人是剃着光头的男人,他们脑顶上都嵌着梅花点儿,身披由布块缝接而成黄色长袍的人,姥姥说:身着黄色百纳衣的叫“和尚”。虹桥虽说地盘不大,尼姑庵,老道观,和尚庙俱全。(同上,164-165页)
令人称奇的是,小镇虹桥曾经举办过妇女“赛脚会”,比一比哪位小姐的“金莲”最小,最美;而“丫头”的姥爷姥姥正是在赛脚会上巧结良缘,成为夫妇的。读了这段故事,真有大开眼界之感。
母亲的脚叫白薯脚。
姥姥是一双金莲脚。
姥姥那双小脚,常使我想起北方农舍房檐下挂着的尖尖红辣椒。据说,在她当闺女的时候,虹桥镇曾有过一次金莲脚的比赛,姥姥的脚虽然够标准的了,但在赛脚会上,却名落孙山,得了个第17名。奖品是一双绣花的金莲鞋和一条红缎子裹脚布。
当时,姥爷已是县里名声显赫的武举人。赛脚会后武把式的弓箭比赛中,姥爷不知为啥马失前蹄,在30步内箭穿巴掌大的铜钱眼的比武中,箭羽不但没有穿过铜钱眼,连铜钱都没碰着,脱弦的箭鬼使神差一般,射穿了围观人群中一个大闺女的葱绿裤脚。姥爷的爷爷认为这是前世结下的缘分,这个皮肤白皙、眉清目秀的大闺女,便是我的姥姥。(同上,206-207页)
4、古人留下的石碑大多竖立在石雕的龟座上,也就是俗话说的“王八驮石碑”。其实,那石座不是龟,更不叫王八,它的学名叫贔屓(bìxìe),只是因为它的样子很像龟,才得了“龟”、“王八”之类的很不雅的外号。旧时,桥梁两端大多竖碑,碑下大多有龟座在,而车把式走到这里都要虔诚地往石龟嘴里抹油,祈求一路平安。这种习俗同样令今人感到新奇。对此,从维熙先生是这样描述的:
“尤其逗我乐呵的,是那三只石龟的嘴里,都油黑油黑地闪着亮光——那是路过五里桥赶大车的车把式,往它嘴里抹的。爷爷说,车把式所以往石龟嘴里抹车油,是怕大车从桥上翻到桥下的河水里去。石龟是路神,司管人间车马的吉凶祸福的。(479页)
我心里打了个冷颤,慌忙跳下龟颈,痴呆地看着那位车把式抽出往车轴上抹车油的刷子,往石龟嘴巴里抹了几抹车油。车把式收起油刷,又正经八本地给那只嘴上粘满车油的石龟,弓身鞠了一躬,口中念念有词:“车行千里路,人马保平安。路神桥神,托您多多保佑!”言罢,才跳上车辕,挥鞭驱车而去。我目送着那辆马车下桥远去,直到车马都淹没在轮下旋起的滚滚的黄尘当中……(486)
5、从维熙的学名和乳名都是他爷爷给起的,他爷爷是个清末秀才,人称“学问篓子”。关于“维熙”这个学名,爷爷说出一番晦涩艰深的道理:按阴阳五行说,从维熙是水命,需要有火字相衬,以达到“水火相济,脱灾化险”的目的,因此以“熙”为名——“熙”字下边的四个点正是个“火”字。从维熙的乳名叫“丫头”。作为唐诗宋词不离口的清末秀才,为什么竟给自己的爱孙起了这么一个粗俗的名字?原来,旧时我们这块土上有个习俗:乳名起得越不雅,小孩活得越结实,寿命越长久。把乳名和学名联系起来看,爷爷一心要让爱孙结结实实地活着。
可是名字起得再好,也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幼年从维熙的健康状况并不是很好,让所有珍爱他的长辈忧心忡忡,于是上演了一出又一出很认真、却又很可笑的“戏法儿”。关于这一点,还是看一看从维熙自己的叙述吧。
“我从病中醒来之后,我看见母亲演出了这样一出我看不懂的戏法儿:她先在碗里倒上半碗水,然后拿来十几根竹筷,一根一根地让筷子在碗里站立.竹筷两头都是圆的,在水碗里站不住,矗下一根,躺倒一根,但母亲十分耐心,不断轮回地在水碗里矗着竹筷……
“我好生不解,正想连珠炮般地向母亲提出我的谜团,一根竹筷居然在碗里笔直地站住了。只见母亲对那碗水里的筷子,高声叫道:“不管你是西天正路上的啥鬼,都快点给我滚开。城隍爷正在召唤你哩!小鬼,你听着,你不该跟着丫头的影儿进我家门,我们从家门儿一向行善积德,丫头又是我的独根苗儿,你快从丫头魂里出来,回你的城隍庙那去!快走--快走……
让人看得开心的是,那根筷子竟在碗里直立不倒。我正乐得眉开眼笑,母亲手拿切菜的菜刀,朝那筷子比划着说:"你还不想走?你不走,我可要下刀了!地狱里的小鬼,我不想让你挨上一刀,你还是乖乖地回城隍庙里去吧!你本已经在阴间里受罪了,我们从家不想叫你罪上加罪。咋样?
不知是母亲挥刀时袖口扇起的风,还是那小鬼被母亲诚意感化了,反正我母亲这番话唠叨过后,那竹筷“叭”地一声,倒在了碗沿上。我母亲扔下切菜刀,挑开门帘,先是拿扫帚扫地,又把那碗里的水泼进灶堂,“咔叭”一声把那筷子折成两截。她回头看着呆看傻了的我说:“丫头!这回你的病就该好了。你罗锅奶奶教我的,这叫驱决定鬼!”(同上,69-71页)
用驱鬼的习俗解除疾病带来的痛苦,具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但在旧社会人们却习以为常。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玉田境内还曾流行这样的“戏法儿”。
6、乳名“丫头”虽然不雅,但是叫惯了听惯了,也就无所谓了。可是,“丫头”七岁那年,姥姥、姥爷和母亲却硬要给他改名为“和尚”,这是为什么?
原来,“丫头”在那年得了一场大病,病了很长时间,差一点丢了小命。病好后,他的样子是“细脖大脑袋”,好像一阵风就可以把他吹出几丈远。为此,经姥爷、姥姥和母亲计议,决定让“丫头”去当“跳墙和尚”。
什么叫“跳墙和尚”?“丫头”的妈妈是这样解释的:一不用受戒——“不用香火头烫出和尚脑瓜上的坑坑点点”,二不到寺庙里去敲木鱼念经,“只当个庙外的和尚,照样吃荤娶媳妇”。丫头不愿去,母亲劝他说:“你只当是去和尚庙玩一趟,给殿上的王爷磕上四个响头,就行了,你这就算当了和尚,佛爷保你无灾无祸。”用姥爷的话说更加明了:“许愿的庙外和尚,不剃成光葫芦,只不过把你脑瓜顶上一撮毛,挪到脑瓜后边去,万一有恶鬼想抓你走,你娘可以从脑后拽着你那撮毛,不叫恶鬼拉着走,那撮毛叫‘拉毛’!”
丫头当“跳墙和尚”的仪式是在虹桥镇海云寺举行的,主持仪式的(也就是师傅)是该寺的方丈云海法师。云海法师用一把“佛剪”,把他原来的瓦片头修理成只有脑后留下一撮毛的“拉毛”头。然后,丫头按照“师傅”的吩咐,去给佛祖如来佛的塑像叩拜。
“记得,我是低垂着头,走到如来佛像前的。迈进大殿门槛时,我有意无意地摸了摸脑后那撮‘拉毛’,觉得自个儿的样儿,一定非常难看。接着,我在云海法师的‘阿弥陀佛’的洪亮声音中跪,对着香烟缭绕的殿堂,不紧不慢的弓着腰磕了四个响头。直到我站起身子,云海法师还在闭合双目、双手合十地面对如来佛叨叨着啥话。与其说为了表示我的心诚,不如说我怕观看殿上的尊尊神像更为确切,我始终耷拉着脑袋,两眼盯着供桌上白馒头尖尖上的红点——那是姥姥为我来当许愿和尚,而连夜蒸出来的,那红点不偏不倚,恰好点在白馒头的正当中……”
“我摸着脑后那撮‘拉毛’,对母亲说:‘鬼来抢我,您可要拉住这撮毛!’
母亲说:‘鬼不敢登门了,你对着如来佛叩头的时候,老和尚把剃下的一绺头发,用黄纸包好,压在了如来佛的脚下;如来佛用佛光罩着你,再厉害的恶鬼也不敢挨近你的身子了。’”(同上,173-174页)
当一番跳墙和尚是否真的可以保障身体健康?这个问题大概属于不可泄露的天机,还是免谈免议为好。但是,丫头脑后的“拉毛”曾经给他带来一些麻烦,却是实实在在、不容怀疑的。特别是在上学后,他的同学们经常揪它拽它,拿跳墙和尚取乐。于是,丫头恳切要求他的姥爷去寺院还俗,他姥爷也便找了几条冠冕堂皇的理由,选了个黄道吉日,到虹桥海云寺找云海法师,剃去了那道“拉毛”。
谁想,在剃掉“拉毛”之后,丫头竟因“回头一望”挨了个“脖儿拐”。
像我“出家”时一样,在香烟缭绕和木鱼声声中,我先叩拜佛祖。剃掉我那撮“拉毛”时,云海法师口吐“善哉善哉”之后,对我还俗提出入世戒言。大意是:不许逆天理纲常。不可争强好胜。不可贪财猎色。不可恶意伤人。不可……我对这些告诫似懂非懂,也只好连连称是。在我接过法师递给我的扫帚,履行打扫佛堂仪式时,云海法师口中又一次念念有词:“阿弥陀佛,吾之扫堂徒儿,前程虽有文曲星引路,但其后颅长有反骨,命中注定一生如履陡壁峭崖。柔智则胜,刚烈则焚;但徒儿维熙大号中,水火相济,互克互补,此乃徒儿终生之幸事也!不知雅号来自于谁?”
法师本是询问姥爷的,我却直起腰来回答说:“爷爷!”
云海法师缓缓睁开闭合双目,对我说道:“徒儿过来!”
我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云海法师又道:“将扫帚递还与我!”
我乖乖地把扫帚交给法师。
“净堂已毕,吾师将赶你出寺了!”云海法师言罢,举起扫帚便向我打来,“你的去路在地阁之西,速速去吧!”
我惊愕了一下,忽然想起这是履行还俗仪式,扭头便跑。先迈过佛堂中一条板凳,以示跳出寺院围墙,然后与姥爷、小姑姑一起逃出寺院山门。姥爷曾叮咛过我,扫堂还俗的寺院和尚,一路不许回头,但当我迈出山门之后,还是情不自禁地回过头来,向云海寺投望最后的一瞥目光。为此,我挨了姥爷一个“脖儿拐”,一巴掌打下来,疼得我脖颈胀痛,接着童心之泉漾出的泪珠,一滴一滴地流了来……(同上,418-419页)
7、在从维熙的《裸雪》中,记载了流行于玉田一带的情趣盎然的儿歌、民谣、小曲等等,这里抄录几段,也许他能唤起许多人特别是中老年人美好的回忆。
1、过年喽 /下雪喽 /河要开喽/ 冰要化喽 /雁要来喽 /树要绿喽/ 鸟要叫喽 /花要红喽……
2、西瓜灯/ 南瓜灯/ 大街小巷挑灯笼/
踢一脚 /踹一脚 /我的灯笼坏不了
3、那边来了白大姐 /又没骨头又没血/ 骑着毛驴挽着纂/ 光着屁股打着伞
4、南来的雁/ 北来的雁/ 在我篮里下窝蛋
5、篷篷车/ 轱辘辘 /里边坐着傻媳妇 / 红盖头/ 葱绿袄/ 屁股底下盘小脚
6、说古迹 /道古迹/ 出门碰见老母鸡/ 母鸡下了九个蛋 /蛋里孵出九只鸡
7、老鹰老鹰你快走/ 一路朝前别回头/ 老鹰老鹰你快飞/ 巢中的小鹰等你归
8、大肚弥勒佛/ 推磨又筛箩 /白雪变白面 /白面蒸白馍
9、头一下抓金/二一下抓银/三抓仍不笑/四才是好人(这是爷爷给丫头哼唱的抓痒小曲)
10、腊月腊/ 冰锥挂/ 小姐绣房里绣梅花 / 东一枝/ 西一枝/ 引来喜鹊登花枝 /元宵圆/ 撑冰船/ 小姐撑船到河南 /东边灯/ 西边灯 /小姐相中状元灯 (这是靠给人挑水维持生计的王柱唱的小曲儿)
11、一个小和尚/ 天天上经堂/ 蒲团身下坐/ 闭眼合巴掌/ 一戒喝烧酒/ 二戒鱼肉香/ 三戒尼姑色/ 四戒娶妻房 /五戒贪银锭/ 六戒出庙墙 /七戒步凡尘/ 八戒想还乡/ 九戒心不诚/ 十戒真和尚(这是狗瘤子叔叔唱的小曲儿)
12、先打免子后打灯/ 百发百中打县城 /刀砍齐燮元 /枪崩殷汝耕/ 哎嘿哎嘿……飞来的骑兵真威风(编者注:齐燮元、殷汝耕都是罪恶累累的大汉奸)。
大盖枪子响砰砰,骑着云彩驾着风。先拿丰润县,后围玉田城。哎嘿,哎嘿……哗啦一声占冀东。(编者注:这是疙瘩爷爷哼唱的抗日小曲儿)。